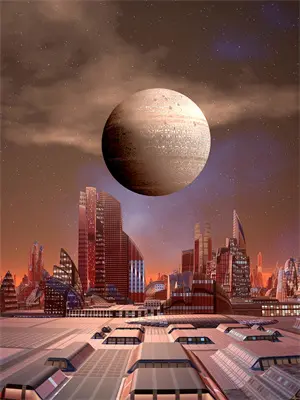
第一章 哭倒北墙,恨上帝王秦朝,长城北段的风跟揣了沙子的鞭子似的,抽了三天还没歇,
天始终灰蒙蒙的,连太阳的影子都见不着。孟姜女跪在塌了半截的城墙根下,
冻得发麻的手指把硬泥抠出两道浅沟,指缝渗的血珠刚冒头就凝了痂。她从江南赶了仨月路,
怀里紧紧揣着半块木刻月牙——那是未婚夫范喜良定亲时刻的,
当时他还拍着胸脯说“等我回来,咱把这月牙拼成整轮的,挂新房窗台上当小灯”,
结果倒好,人没盼回来,只剩她对着一堆混着碎砖的尸骨,扯着嗓子喊人。“范喜良!
你这说话不算数的呆子!答应好的回家,咋还赖在这儿不动了?
”她哭得不似别家姑娘那样抽抽搭搭,反倒像跟城墙置气,
带着股江南姑娘特有的“轴劲儿”,把北长城的沉闷都给冲散了些。
这动静飘到不远处的瞭望台,台上站着个穿玄色龙纹锦袍的主儿,墨发用玉冠束得整整齐齐,
侧脸线条冷得像块玉,正是微服视察的秦始皇嬴政。“陛下,这姑娘哭得实在扎耳朵,
要不臣把她请远点儿?”随从凑上前,刚要挪步,就被嬴政一个眼神定在原地。
嬴政的目光落在那抹蓝布身影上——这姑娘跪在泥里,脊梁却挺得跟刚栽的小树苗似的,
风刮得她头发乱飞,愣是没弯一下腰。他见多了低头哈腰喊“陛下圣明”的人,
头回见哭都哭得这么“理直气壮”的,倒觉得新鲜。“让她哭。”嬴政的声音沉乎乎的,
却没什么火气,“哭倒了朕的墙,总不能拍拍屁股就走,得有个说法。
”孟姜女从大清早哭到天擦黑,嗓子哑得跟被砂纸磨过似的,才一屁股瘫在地上。
她摸出怀里的木月牙,指尖反复蹭着光滑的边儿,眼泪“啪嗒啪嗒”掉在木头上,
晕出一小片湿痕。正揉着发红的眼睛,一双绣着云纹的玄色靴“咚”地停在她眼前。她抬头,
撞进一双深不见底的眼睛——男人居高临下地看着她,眼神亮得像寒星,
却没半分凶巴巴的样子。“哭够了?”嬴政开口,语气比北地的风柔和些,
“把朕的城墙哭塌了,这笔账,你打算怎么还?”孟姜女攥紧木月牙,撑着胳膊慢慢站起来,
膝盖蹲得发麻,却还是梗着脖子:“要杀要罚我都认!就求陛下开个恩,
让我把范喜良的骨头带回去,送他回江南老家。”“范喜良?”嬴政眉梢挑了挑,
想起早上随从递的纸条——半月前北段有个姓范的书生,累得倒在工地上,没救过来,
骨头已经砌进城墙了。他瞅着孟姜女红通通的眼睛,忽然改了主意:“想带他走也成,
但你得留在朕身边当侍从,抵了这塌墙的债。啥时候朕觉得够了,就放你带着他回家。
”孟姜女懵了——她还以为要被拖去打板子,没想到是这么个安排。她盯着嬴政冷生生的脸,
心里恨得牙痒痒:要不是你修这破长城,喜良能死在这儿?可眼下,只有跟着他,
才能把喜良的骨头找着。“……我答应。”她咬着牙应了,声音还有点不服气,
“但我可说好了,我留在这儿,就为了喜良,可不是服你这个皇帝!”嬴政没接话,
转身往马车走。风掀起他的锦袍角,孟姜女看着那道挺拔的背影,
心里暗暗嘀咕:等把喜良的骨头找着,我立马卷铺盖走人,
再也不跟你这“祸头子”帝王沾边!偏他来时不逢月第二章 针锋相对,
暗生暖意孟姜女成了嬴政身边最“特殊”的侍从——不跪不拜,不凑跟前献殷勤,
每天揣着那半块木月牙,跟在嬴政身后三米远,活像个自带“生人勿近”牌子的小尾巴。
嬴政倒也不较真,依旧给她留着单独的帐篷,三餐按随从标准来,
甚至特意让人多添了碗热汤——北地冷,怕她这江南姑娘扛不住。可孟姜女不领情,
汤是喝了,却总在嬴政看过来时,故意把脸绷得跟城墙砖似的,仿佛碗里盛的不是热汤,
是“御赐罚酒”。随从都偷偷捏把汗,私下劝她:“姑娘,陛下可是天子,您多少顺着点,
别总跟对着干似的。”孟姜女头一扭:“我又没做错事,凭啥要顺着?要不是他修长城,
我家喜良能……”话说到一半,又咽了回去,指尖攥紧了怀里的木月牙。
这天视察北长城的粮草营,刚进门就听见吵嚷声。几个民夫围着粮官要粮食,
其中一个瘦得只剩骨头的老汉,抱着粮官的腿哭:“大人行行好,给口吃的吧,
我儿子快饿晕了!”粮官不耐烦地踹开他:“急什么?粮草还没运到,再等等!
”老汉被踹得趴在地上,半天没爬起来。孟姜女看得火冒三丈,忘了自己“侍从”的身份,
冲上去就拦在老汉前头:“你怎么能打人?他们都快饿死了,你还拿架子!”粮官愣了,
转头看见嬴政,立马换了副谄媚脸:“陛下恕罪,这老东西胡搅蛮缠,臣只是……”“闭嘴。
”嬴政打断他,目光落在老汉冻得发紫的手上,又扫过粮囤——角落里明明堆着几袋粟米,
却蒙着布,像是故意藏着。他没发火,只对随从说:“打开粮囤,先给民夫们分些粟米,
再传朕的令,让后续粮草加快运送,不许再延误。”粮官脸都白了,赶紧让人照做。
老汉捧着热乎的粟米,对着嬴政磕头谢恩,
孟姜女也愣在原地——她以为这帝王只会下令修长城、征民夫,
却没想他会为几个素不相识的民夫,驳了粮官的面子。从粮草营出来,风刮得更紧了,
卷着沙砾往人脸上扑。孟姜女被吹得睁不开眼,头发乱得跟草似的,几缕碎发糊在脸颊上,
还沾了点沙尘。她正抬手想拢,就见嬴政抬手唤来随从,递过去一方干净的绢帕:“给她,
让她把头发擦干净,别沾着沙子冻着头皮。”随从把绢帕递过来,孟姜女接过时,
指尖不小心碰到了绢帕——还带着点温热,想来是嬴政揣在怀里暖着的。
她捏着软乎乎的绢帕,心里忽然有点发慌,赶紧低下头擦头发,避开了嬴政的目光,
耳尖却悄悄红了。那天之后,孟姜女对嬴政的态度,悄悄松了些。
她不再故意跟嬴政保持三米远,会主动递上温好的茶水;嬴政看奏折到深夜,
她会在帐篷外留一盏灯,还多添了个暖炉;甚至有次嬴政不小心被城砖绊倒,
她想都没想就冲上去扶,虽然扶完就赶紧退后,却忘了绷脸,耳根子还红着。
嬴政把这些变化看在眼里,心里像被温水泡过似的,软了些。有天夜里,两人坐在篝火旁,
孟姜女正低头磨着木月牙,嬴政忽然开口:“范喜良……是个什么样的人?”孟姜女手一顿,
眼神柔和下来:“他是个书生,手笨,刻这月牙时磨破了好几次手指,
却还笑着说‘要刻得最圆,才配得上你’。”嬴政看着她眼底的温柔,心里有点发涩,
却还是说:“朕已经让人去查他的尸骨位置了,很快就有消息。”孟姜女抬头看他,
篝火的光落在他脸上,柔和了他平日里冷硬的线条,竟少了几分帝王的威严,
多了些常人的温度。“谢谢陛下。”她轻声说,声音里没了之前的僵硬,多了点真心实意。
几天后,嬴政受了风寒,夜里发起高烧。随从们急得团团转,孟姜女却悄悄去了灶房,
按江南的法子煮了碗姜汤,还放了点驱寒的草药。她端着姜汤走进帐篷时,嬴政正靠在榻上,
脸色发白,眉头紧锁。“陛下,喝碗姜汤吧,能退些烧。”嬴政睁开眼,看见她手里的陶碗,
眼神里闪过惊讶,随即接过,一口口喝了下去。温热的姜汤滑过喉咙,暖了身子,
也暖了心里某个角落。“你怎么知道这方子?”他问。“我娘教的,以前我感冒,
她就煮这个给我喝。”孟姜女低着头,小声补充,“陛下是大秦的天子,可不能病倒了,
不然……百姓们就没人护着了。”嬴政看着她泛红的耳尖,忽然觉得,这北长城的风,
好像也没那么冷了。他知道,孟姜女心里还装着范喜良,也还记着长城带给她的伤痛。
可这份悄然滋生的暖意,就像篝火里的火星,虽微弱,却慢慢燃了起来——他是帝王,
习惯了孤独与威严,却偏偏对这个带着“恨”来、却渐渐显露真心的姑娘,动了心。
只是他也清楚,这份心动,注定裹着荆棘——一边是她对亡夫的执念,一边是他帝王的身份,
还有那道横亘在两人之间的长城,沉甸甸的,压着不敢说出口的情意。
偏他来时不逢月第三章 骨消息至,心意难藏孟姜女对嬴政的态度软下来后,
北长城的日子少了针锋相对的紧绷,多了些润物无声的暖意。她不再刻意与他保持距离,
清晨会提前温好茶水装在竹筒里,递过去时语气平静:“陛下,晨间风大,喝口热茶暖身子。
”傍晚嬴政归来,帐篷里的暖炉总添足了炭火,
案上还摆着刚热好的干粮——她记得他常因看图纸忘了吃饭。就连他对着工事图皱眉时,
她也会端来一碗莲子羹,直言:“陛下盯图纸久了伤神,先歇会儿再看。”没有忸怩,
没有躲闪,她的转变带着江南女子的通透——恨归恨,可嬴政帮她找喜良、护她在北地安稳,
这份情她记着。只是夜里独处时,
想起他递茶时指尖的轻触、看她时眼底的沉敛、替她挡开乱闯民夫时的背影,
心里会泛起一丝说不清的波澜。她告诉自己,这是感激,不是别的——喜良还在等她,
她不能对“罪魁祸首”有旁的心思。而嬴政,将她的转变看在眼里,心里自有一番考量。
他是帝王,习惯了权衡利弊,从不做无意义的事。起初留她,是好奇她哭倒城墙的执拗,
后来见她护民夫、念旧情,倒觉得这女子比朝堂上的趋炎附势之辈更鲜活。
他不动声色地对她好——让人从江南调来她爱吃的蜜饯,
放在案边最顺手的位置;她磨木月牙时,默默递过细砂纸;夜里她帐内灯灭得晚,
便让随从多备一盏防风灯送去。他从不说破这份心思,只以“抵债”为借口,将她留在身边。
帝王的喜欢从不是小儿女的直白,是藏在细节里的纵容,
是不动声色的关照——他知她心里有范喜良,便不逼、不催,只在她需要时,递上一份安稳。
这天午后,贴身随从匆匆找到孟姜女,语气恭谨:“孟姜姑娘,陛下唤您去帐中,
说是范公子的尸骨有消息了。”孟姜女手里的木月牙“啪”地掉在地上,她弯腰去捡,
指尖却控制不住地发颤:“真……找到了?”“是,陛下让人查了半月,
终于在北段城墙西侧,找到手骨带疤的尸骨,与您描述的范公子特征完全吻合。”随从点头。
孟姜女攥着木月牙,快步走向嬴政的帐篷。掀帘而入时,嬴政正坐在案前,
手里捏着一份勘验记录,见她进来,缓缓放下笔,神色比平日柔和几分,
却依旧带着帝王的沉稳。“来了?”他指了指案上的纸条,“尸骨位置已确认,
手骨疤痕清晰,错不了。”孟姜女走到案前,目光落在纸条上,
眼泪却先一步砸了下来——不是哭倒城墙时的刚烈,是积压了数月的思念与释然,
混着一丝莫名的慌乱,让她喉头发紧。嬴政递过一方绢帕,是之前那方,被她洗得干净,
叠得齐整放在案角。“哭吧,找到他了,该高兴。”他声音平稳,听不出情绪,
只有他自己知道,指尖捏着绢帕的一角,微微发紧。孟姜女接过绢帕,擦了擦眼泪,
语气里有感激,也有几分复杂:“谢谢陛下,若不是您,我怕是……一辈子也找不到喜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