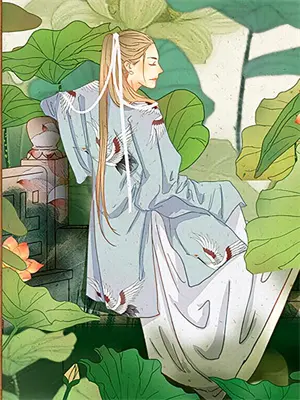
我是他的皇后,他却亲手喂我喝下堕子汤。十年相伴,他登基后第一件事就是诛我全族。
冷宫里,我用碎瓷片刮掉他当年刻在我腕上的情字。血尽之时,
…”我笑着在他耳边咳血:“别怕…下一个被诛全族的…该是你的新宠了…”1我死的那天,
雪花正悄然覆盖冷宫的破败屋檐。寒意渗入骨髓,与我残存的意识做着最后的纠缠。
我知道自己快要死了,手腕上的伤口已经不再流血,生命正随着体温一点点消散。
这冷宫四壁陡然,唯有窗外飘落的雪陪伴我走完最后一程。他冲进来时,
我已只剩最后一口气。那声撕心裂肺的“不——”成了我在这人世听见的最后声音,
裹挟着无尽悔恨与绝望,在冷宫四壁间撞击回荡。多可笑啊,萧衍。亲手将我推入地狱的人,
此刻却扮作痛失所爱的痴情郎。灵魂脱离躯壳的瞬间,我没有升入天堂,也未堕入地狱,
而是悬浮在冷宫梁木之间,俯瞰着下方那出由他自导自演的戏剧。恨意如铁链将我禁锢于此,
我发誓要亲眼看着这个毁了我一生的男人,如何被自己的所作所为反噬。萧衍,我的夫君,
大梁的皇帝,正跪在冰冷的地面上,将我早已冰冷的身体紧紧搂在怀中。
他的眼泪落在我灰白的面颊上,又迅速凝结成冰。龙袍上沾满从我手腕伤口渗出的暗红血迹,
那颜色比凤仪宫最华贵的胭脂还要刺目。“阿谢...醒醒...”他语无伦次,
颤抖的手指一遍遍拂过我的眼皮,徒劳地试图让那双再也无法睁开的眼睛再次看他一眼。
那双手,曾温柔地抚过我的发,也曾坚定地喂我饮下那碗夺去我们孩子的毒药。我冷眼旁观,
心中再无波澜。这个曾让我倾尽所有去爱的男人,
如今在我眼中不过是个可悲的傀儡——被权力与猜忌蚕食了灵魂的傀儡。“传御医!
全都给朕拖过来!”他嘶吼着,额角青筋暴突,帝王的威仪荡然无存。
那声音里的恐慌如此真实,几乎让我又要信了——若我不是刚刚亲历过他赐予的死亡。
没人敢动。所有人都明白,榻上那人早已气息全无,身体都开始僵硬了。
几个老御医交换着眼神,那目光中除了恐惧,还有一丝不易察觉的怜悯——为我也为他。
他吼了几声,得不到回应,那癫狂的怒火骤然熄灭,转化为更深沉的绝望。
他将脸深深埋在我冰冷的颈窝,肩膀剧烈颤抖,发出被剜心般的呜咽。像一头受伤的孤狼。
多可笑。亲手将我推入死亡之境的人,此刻却为我的死悲痛欲绝。这深宫中的爱恨,
从来都是如此荒唐可笑。他抱着我,就那么跪在冰冷的地上,许久许久。
久到风雪再次透过破窗呼啸而入,将他明黄的龙袍染上白霜。
久到闻讯赶来的御医跪满一院子,在寒风中抖如筛糠,无人敢出声。
久到...天色由浓黑转为灰白。他终于动了。缓缓地,极其缓慢地抬起头。一夜之间,
他仿佛苍老了十岁。面容憔悴灰败,眼底是一片干涸的血色和荒芜,
再找不到往日深沉锐利的帝王光芒。这一刻,他不是皇帝,只是个失去一切的可怜人。
他小心翼翼地将我放回炕上,笨拙地扯过那床潮湿发霉的旧被,想为我盖上,手却抖得厉害,
几次都无法将被子展平。那双手曾经执掌生杀大权,此刻却连一床薄被都整理不好。最终,
他放弃了。他的目光落在我垂在炕沿的右手,和那片掉落在旁的、沾着干涸血迹的碎瓷片上。
他伸出手,指尖颤抖着,拾起那片碎瓷。粗糙的边缘深深嵌进他的掌心,
鲜红的血珠瞬间涌出,顺着手腕滴落。他却仿佛感觉不到疼痛,只是死死攥着它,
像是要从中攥出什么早已消散的温度。然后,他看见了。
看见了我腕间被他亲手攥裂的伤口处,布帛松散,
露出底下狰狞扭曲的疤痕——那个曾经刻着“情”字的地方。如今,
只剩一片模糊丑陋的肉痂,诉说着当时剥离的决绝与惨烈。我曾用这片碎瓷,一刀一刀,
将那个他亲手刻下的字连血带肉地剜去。每一下,都伴随着回忆的凌迟。记忆如潮水般涌来。
那年桃花树下,他执起我的手,在那纤细的腕内侧,用特制的金针沾着朱砂,
一笔一划刻下那个“情”字。“阿谢,我要你永远记住,今生今世,我萧衍只对你一人动情。
”我疼得眼泪汪汪,他却温柔地吻去我的泪珠:“这点痛算什么?我要这字融入你的骨血,
来世也能凭着这个找到你。”当时只觉得甜蜜无比,如今想来,早在那时,
他就已经开始在我的血肉之躯上刻写他的所有权。我不是他的妻,只是他的一件所有物,
可以随意刻印,也可以随意摧毁。他像是被惊雷劈中,整个人猛地僵住,瞳孔缩成针尖,
呼吸停滞。那片碎瓷从他颤抖的指间再次滑落,“嗒”一声轻响,在死寂的宫中格外清晰。
这一次,他没有去捡。他只是怔怔地、绝望地看着我那截伤痕累累的手腕,看着那片空无。
仿佛直到此刻,他才真正明白,他失去的究竟是什么。不仅仅是一个曾经深爱他的女人,
一个未出世的孩子,一个忠心的家族。他亲手毁掉的,
是他自己曾拥有过的、最后一点鲜活的热气,是这孤家寡人生涯里,
唯一一点不必猜忌、无需权衡的真情。如今,什么都没了。
只剩下这座冰冷的、用至高权力和无边孤寂浇筑的黄金牢笼。
和掌心那道永难愈合的、源自一片碎瓷的伤口。他缓缓站起身,身形踉跄,几乎站立不稳。
内侍慌忙想去搀扶,却被他一个眼神骇得倒退数步。那眼神,空得吓人。他不再看榻上的我,
也不再看任何人。只是一步一步,朝着殿外走去。背影佝偻,仿佛背负千钧重担,
每一步都踩在刀尖上。走到门口,风雪灌入,吹得他明黄袍袖猎猎作响。他顿住脚步,
没有回头。只是极轻极轻地,对跪了满院的御医和内侍说了一句。声音沙哑得如同砂纸磨过,
没有任何情绪,却让所有听见的人,从骨头缝里渗出寒意。“皇后...薨了。
”“按...旧例办。”旧例?哪个旧例?是原配皇后的风光大葬?
还是废后庶人的草席裹身?无人敢问。他踏出冷宫门槛,
走入那片灰白的天光与未尽的风雪中。再也没有回头。***我的魂魄没有离去,
而是在这深宫徘徊。恨意如锁链,将我的灵魂禁锢在这座吃人的宫殿中。
我看见云鬓扑在我冰冷的身体上,发出最后一声绝望的哀泣,彻底昏死过去。
她那曾经圆润的脸庞如今瘦削得吓人,眼角深深的纹路记录着这些时日来的煎熬。
我多想再摸一摸她的发,告诉她好好活着,却只能眼睁睁看着宫人将她抬走。
云鬓是我从谢家带进宫的贴身侍女,自我十五岁嫁入王府就跟着我。那年春猎,
我险些被失控的马匹甩下山崖,是云鬓死死拽住缰绳,双手被磨得血肉模糊也不肯放手。
从此我将她视为姐妹而非奴婢。“娘娘,云鬓会永远护着您的。”她曾经这样发誓,
而她也确实做到了。即使在我被废入冷宫,所有人都避之不及的时候,
只有她想方设法打点守卫,偷偷给我送吃的用的。我记得最后一次见她,
她偷偷塞给我一个还温热的馒头,自己却瘦得颧骨高突。
我质问她是不是把口粮省下来给我了,她只是笑:“奴婢不饿,娘娘您要保重身体,
总会有翻身的那天的...”可笑,我最终还是没有等到那天。我看见内侍们面面相觑,
不知该如何处置我的尸身——按废后庶人之礼,还是按陛下那句模糊的“旧例”?最终,
他们折中取了个方式,将我用一床稍好的被子裹了,抬出冷宫,安置在一处偏僻殿宇。
那里比冷宫好些,至少没有漏风的窗,但依然冷清得可怕。没有人来装殓,没有人来悼念。
仿佛我只是宫中一片落叶,悄无声息地飘零、腐烂。曾几何时,我还是那个母仪天下的皇后,
凤仪宫中终日人来人往,如今却落得如此凄凉的结局。我记得封后大典那天,
萧衍牵着我的手,一步步走上白玉阶。他侧过头,在我耳边轻语:“阿谢,从今往后,
这江山有我一半,就有你一半。”我笑靥如花,以为那是世间最美的情话。殊不知,
帝王的情话,从来都是裹着蜜糖的毒药。第三天,萧衍来了。他屏退左右,
独自站在我的尸身前,久久不语。我的身体已经开始发生变化,但他似乎毫不介意,
只是站在那里,一动不动,仿佛一尊雕塑。“阿谢,”他终于开口,声音嘶哑得不成样子,
“柳家的事,朕查清了。”他轻笑一声,那笑声里满是苍凉:“根本没有密信,对不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