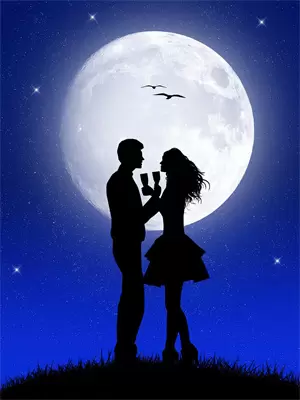第1章 霜降巷口的初遇霜降过后,老城区的风就裹上了凉劲儿,却没把梧桐叶吹得蔫掉,
反倒催着它们染了金,风一吹,就打着旋儿飘下来,铺在拾光旧书店的木质门阶上,
像给奶白色的门头镶了圈暖黄的边。林晚秋蹲在门口扫落叶,
竹制扫帚的枝桠轻轻划过高门槛,带起的风惊飞了趴在台阶上打盹的橘猫。
林晚秋把扫到一起的落叶拢进竹筐里。指尖碰到一片还带着潮气的梧桐叶,
她忍不住捡起来捏了捏——叶片厚实,脉络清晰,像极了外婆当年压在书里的那些书签。
书店是外婆传下来的,藏在老巷最深处,门头的奶白色漆褪了些色,
露出底下浅棕的木头纹理,反倒多了点岁月的软劲儿。橱窗里摆着几本封皮泛黄的旧书,
最显眼的位置放着个铜制小台灯,灯杆上缠了圈细细的麻绳,是外婆生前缠的。
每天早上七点,林晚秋都会把灯打开,暖黄的光透过玻璃,在清晨的老巷里晕开一小片亮,
成了巷子里老住户们晨起的“路标”——看见这盏灯亮着,就知道书店开门了,
想买本旧书、唠两句家常,都能往这儿来。把竹筐提到巷口的垃圾桶旁,
林晚秋刚转身要回店,就看见巷口站着个穿米白色针织衫的男生。他手里拎着个黑色帆布包,
包带磨得有些毛边,却洗得干干净净;怀里抱着本摊开的五线谱本,指尖正轻轻点着纸页,
指腹蹭过音符时,动作轻得像怕碰坏了什么。男生的头发软软地搭在额前,
碎发被风吹得微微晃,遮住了一点眉眼,却挡不住眼底的温和,他的目光落在书店门头上,
带着点犹豫,像在纠结要不要过来。林晚秋愣了一下。老巷里就那么十几户人家,
大多是住了几十年的老街坊,彼此都熟得能叫出对方家孩子的小名,这张脸倒是陌生得很,
看着像刚搬来的。她走过去,脚步放得很轻,怕打扰到对方默记旋律,轻声问:“请问,
你是要找什么地方吗?”男生听见声音,立刻转过头来,眼底的犹豫瞬间褪去,
换成了浅浅的笑意,像把凉风吹散了大半:“你好,我是来问下,
这家书店……可以进去坐一会儿吗?我想抄点乐谱,外面风有点大,怕吹乱了纸页。
”他的声音很轻,像钢琴上轻轻落下的低音do,带着点温润的质感,落在耳边不吵,
反倒让人觉得安心。林晚秋顺着他的手看向五线谱本,纸页上画着密密麻麻的音符,
还有几处用铅笔标注的修改痕迹,线条很细,看得出来下笔的人很细心。她点点头,
往旁边让了让,把门口的位置让出来:“可以的,进来吧。里面有靠窗的桌子,晒得到太阳,
暖和。”“谢谢。”男生笑着道谢,抱着五线谱本跟她走进书店。书店里没装空调,
只在墙角放了个加湿器,雾蒙蒙的水汽里混着旧书特有的油墨香,
还有薰衣草的淡香——是林晚秋早上刚加的精油,外婆以前说过,
薰衣草的香味能让人静下心来,适合看书。书架是深棕色的实木,从地面一直顶到天花板,
格子里摆满了各式各样的旧书,有的书脊上的字磨得看不清了,
林晚秋就用小纸条重新写了贴上去;有的书缺了页,她就找了相似的纸,
照着外婆留下的笔记补全。书架最上层摆着几个铁皮盒,里面装着外婆当年收集的书签,
有梧桐叶的,有银杏叶的,还有用彩纸折的小纸船。林晚秋把他引到靠窗的桌子旁,
那是外婆以前常坐的位置,桌子上还留着一道浅浅的划痕,是小时候她调皮,用铅笔划的。
她转身去收银台倒了杯温水,杯壁是淡蓝色的陶瓷,上面印着个小小的猫咪图案,
也是外婆留下的。“你坐这儿吧,台灯可以打开,光线好点。”她把水杯递到男生手里,
又指了指桌角的台灯,“要是不介意,也可以看看书架上的书,都是旧书,不过都能看,
就是翻的时候轻点,别把书页弄掉了。”“谢谢,我肯定小心,不打扰你做生意就好。
”男生接过水杯,指尖碰到杯壁,温温的触感传过来,他轻轻说了句,“我叫沈知言,
就住在前面的梧桐巷,上周刚搬来,是个钢琴师,最近在整理外婆当年留下的乐谱,
想找个安静的地方抄录,转了好几条巷,就看见你这家书店了。”“林晚秋,
这家书店的店主。”她笑着自我介绍,又指了指趴在书架旁打盹的阿橘,“那是阿橘,
去年冬天捡的流浪猫,不咬人,你不用怕它,要是它凑过来,就是想让你摸它。
”沈知言看了眼阿橘,阿橘也刚好醒了,抬头看了他一眼,尾巴轻轻晃了晃,又低下头,
把脸埋进爪子里继续打盹。他忍不住笑了笑,眼底的温柔更浓了些:“阿橘,名字真好听,
跟它的毛很配。”说着,他从帆布包里拿出一支黑色的钢笔,笔身是磨砂的,
看着用了有些年头,又把五线谱本摊在桌上,小心翼翼地抚平纸页,
打开台灯——暖黄的灯光落在纸页上,把黑色的音符照得格外清晰,
连铅笔标注的细小符号都能看清。林晚秋没再打扰他,转身回到收银台后。
收银台是个旧木柜,上面摆着外婆留下的老旧收音机,外壳是深棕色的,掉了块漆,
却还能用,偶尔林晚秋整理书累了,就打开听听,大多是些老曲子。
她拿起一本没看完的旧书——《城南旧事》,封皮是浅灰色的,里面夹着张梧桐叶书签,
是去年秋天捡的,已经压得很平整。书店里很安静,只有她翻书的“沙沙”声,
还有沈知言钢笔划过五线谱本的轻响,偶尔夹杂着阿橘的呼噜声和加湿器的细微水声,
格外惬意。风从窗户缝里钻进来,吹得台灯的光晕轻轻晃,落在书架上,
把旧书的影子拉得长长的。中途林晚秋起身整理书架,
最下层的几本童话书被昨天来的小朋友翻乱了,她蹲下来,一本本把书摆整齐。
路过沈知言身边时,忍不住瞥了眼他的五线谱本。纸页上的音符排列得整齐又好看,
像一群站着队的小矮人,修改的痕迹也很轻,不像她写东西,总爱涂涂画画,
把纸页弄得乱糟糟的。沈知言察觉到她的目光,没抬头,
只是轻声说:“这是我外婆当年留下的乐谱,有些地方受潮模糊了,想抄录下来,
以后弹给人听。”林晚秋停下脚步,轻声问:“是钢琴曲吗?”她外婆以前也喜欢听钢琴曲,
小时候她总趴在外婆腿上,听外婆用老旧的收音机放肖邦的夜曲,收音机里的声音有点模糊,
却成了她童年里最温暖的背景音。“嗯,都是很老的曲子,外婆以前经常弹给我听。
”沈知言这才抬头,眼神柔和下来,像落了层暖光,“我小时候总爱趴在钢琴上,
看外婆弹琴,后来外婆走了,我就开始学钢琴,想着以后能把她的曲子弹完。
”林晚秋点点头,没再多问。她知道,旧东西里都藏着故事,就像她的旧书店,
每一本旧书里都可能夹着前主人的心事;就像沈知言的旧乐谱,
每一个音符里都装着他对外婆的念想。问多了,反倒会惊扰了这份藏在时光里的温柔。
她转身继续整理书架,指尖划过一本封面印着黑色钢琴的旧书时,忍不住停了下来。
那是一本《钢琴名曲赏析》,封皮有点磨损,书脊上的字掉了两个,
还是外婆当年特意找修书的老师傅补的。里面还夹着一张泛黄的书签,
是外婆年轻时用梧桐叶压的,叶片已经脆了,林晚秋每次翻这本书,都格外小心。
等她整理完书架回到收银台,就看见沈知言正看着那本《钢琴名曲赏析》,
眼神里带着点惊讶,像看到了什么熟悉的东西。“你也有这本书?”他抬头看向林晚秋,
声音里带着点不可置信,“我外婆的书架上,也有一本一模一样的,
封皮磨损的地方都差不多。”林晚秋走过去,把书递给他:“是我外婆留下的,
她以前喜欢听钢琴曲,这本书她翻了很多遍,里面还有她用红笔标出来的重点,
说这些曲子最适合晚上听。”沈知言接过书,手指轻轻捏住书脊,没敢用力,
怕把脆弱的书脊弄断。他轻轻翻开扉页,
果然在右上角看到了一行娟秀的字迹——“苏晚卿”,字迹有点褪色,却依旧清晰。
旁边还有几处用红笔标注的曲子名称,比如《月光奏鸣曲》《小夜曲》,
标注的符号跟他外婆书上的一模一样。他的指尖轻轻蹭过扉页上的字迹,眼神里满是温柔,
像在跟老朋友打招呼:“我外婆叫沈清如,她的那本《钢琴名曲赏析》上,也有这样的标注,
没想到这么巧。”林晚秋愣了一下,苏晚卿是外婆的名字,她从小听到大,
却没想到会在外人的口中,跟“巧合”联系在一起。窗外的梧桐叶又落了几片,
顺着玻璃滑下来,落在窗台上,发出轻轻的声响。她看着沈知言认真翻书的模样,
又看了看桌上摊开的五线谱本,忽然觉得,这个霜降后的下午,
好像比以往任何一个下午都要暖——就像旧书遇见了懂它的人,
就像旧乐谱遇见了能弹它的人,她的旧书店,好像也遇见了一个特别的人。
沈知言翻到书的中间,忽然停了下来,指着一页上的批注说:“你看,
我外婆也在这页写了‘冬日围炉听最宜’,跟你外婆的批注一模一样。”林晚秋凑过去看,
果然,外婆用蓝笔写的批注旁边,沈知言外婆的红笔批注像在呼应,字迹不同,
却藏着同样的喜好。她忍不住笑了:“好像她们俩早就认识一样。”“说不定真的认识呢。
”沈知言也笑了,把书轻轻合起来,放回原位,“老城区的巷子里,以前住的人不多,
说不定她们年轻时还一起弹过钢琴、看过书。”这话像一颗小石子,落在林晚秋心里,
漾开了一圈圈涟漪。她以前总听外婆说,年轻时有个很要好的闺蜜,两人都喜欢钢琴,
后来闺蜜搬去了别的地方,断了联系,外婆还难过了好久。
她一直以为那只是外婆随口提的往事,没想到今天,竟能从沈知言的口中,找到一点线索。
直到傍晚六点,天色渐渐暗下来,沈知言才抄完乐谱。他把乐谱和钢笔放进帆布包,
又把桌上的台灯关掉,仔细把五线谱本叠好,放进包里。转身时,
他又看了眼那本《钢琴名曲赏析》,才对林晚秋说:“今天谢谢你,让我在这里抄乐谱,
还跟我聊了这么多。明天我还能来吗?还有几页没抄完,
外面实在找不到这么安静又暖和的地方了。”林晚秋点点头,笑着说:“可以啊,
随时来就行。我每天七点开门,你要是来早了,就在门口等会儿,或者跟阿橘玩一会儿,
它很喜欢跟人待在一起。”沈知言看了眼趴在桌上打盹的阿橘,阿橘像是听到了自己的名字,
抬了抬头,又低下头去。他忍不住笑了:“好,那明天见,林晚秋。”“明天见,沈知言。
”看着沈知言的身影消失在巷口,林晚秋才收回目光。她走到靠窗的桌子旁,
拿起沈知言没喝完的水杯,杯壁上还残留着他的温度,温温的,像他的声音一样。
她又拿起那本《钢琴名曲赏析》,轻轻翻开扉页,指尖蹭过外婆的字迹,
又想起沈知言外婆的名字——沈清如,心里忽然生出一种莫名的期待,
期待明天沈知言的到来,期待能听到更多关于乐谱、关于两位外婆的故事。
阿橘慢悠悠地走过来,趴在桌上,用脑袋蹭了蹭她的手。林晚秋摸了摸阿橘的头,
轻声说:“阿橘,明天他还会来哦,以后咱们书店里,就不止咱们俩了。
”窗外的天色彻底暗下来,林晚秋打开橱窗里的铜制台灯,暖黄的光又亮了起来,
照亮了书架上的旧书,
也照亮了桌上那本还带着余温的五线谱本——那是沈知言收拾东西时不小心落下的,
纸页上还留着他钢笔的字迹,清晰又温柔。第2章 晨光里的日常羁绊第二天早上,
林晚秋比平时起得早了半小时。她煮了两碗粥,一碗自己喝,一碗盛在浅口瓷碗里,
放在靠窗的桌子上,旁边还摆了一碟腌萝卜——昨天听沈知言说,他早上喜欢喝清淡的粥,
她就特意多煮了点。把阿橘的猫粮倒在食盆里,林晚秋又去整理橱窗,
把昨天被风吹歪的旧书摆正,又给铜制台灯换了新的灯泡,确保暖黄的光能稳稳地亮着。
做完这一切,她看了眼墙上的挂钟,才六点五十五分,离七点还有五分钟。
她搬了个小凳子坐在门口,手里拿着片刚捡的梧桐叶,轻轻擦着上面的灰尘。
风从巷口吹过来,带着清晨的凉意,却不刺骨,梧桐叶在手里轻轻晃,像在跟她打招呼。
“林晚秋?”熟悉的温润嗓音从巷口传来,林晚秋抬头,就看见沈知言走了过来。
他今天穿了件浅灰色的卫衣,外面套了件黑色的薄外套,手里拎着帆布包,
怀里还抱着个保温袋,看见她坐在门口,笑着加快了脚步。“你怎么这么早?
”林晚秋站起来,把凳子往旁边挪了挪,“我刚准备开门。”“怕来晚了,
靠窗的位置被人占了。”沈知言笑着说,把怀里的保温袋递到她手里,“我早上煮了点红薯,
想着你可能没吃早餐,就给你带了一块,甜的,不烫。”林晚秋接过保温袋,指尖碰到袋子,
能感受到里面的温度,心里也跟着暖了起来:“谢谢,我刚好煮了粥,放在里面了,
你要是不嫌弃,就一起吃点。”“不嫌弃,求之不得。”沈知言跟着她走进书店,
刚放下帆布包,阿橘就凑了过来,用脑袋蹭他的裤腿,“喵”了一声,像是在欢迎他。
“你看,阿橘果然喜欢你。”林晚秋笑着说,把粥端到桌上,
又把沈知言带来的红薯放在碟子里,“快坐吧,粥还温着,红薯也趁热吃。”沈知言坐下,
拿起勺子喝了口粥,米香很浓,还放了点小米,喝起来暖暖的,刚好驱散了清晨的凉意。
他又咬了口红薯,甜糯的口感在嘴里散开,没有丝,很软:“你煮的粥真好吃,
比我煮的强多了,我上次煮粥,把锅底都煮糊了。”林晚秋被他逗笑了:“慢慢来,
煮粥只要看着火,别让它溢出来就行。你平时一个人住吗?”“嗯,
上周刚从学校附近搬过来,梧桐巷的房子是我外婆留下的,一直空着,
我想着整理一下住进来,也能方便整理她的乐谱。”沈知言说着,
从帆布包里拿出昨天落下的五线谱本,有点不好意思地说,“昨天不小心把这个落在这儿了,
没耽误你吧?”“没耽误,我昨天收拾桌子时看到了,就给你收起来了。
”林晚秋从收银台里拿出五线谱本,递到他手里,“你今天继续抄?“嗯,还有最后几页,
抄完就能把乐谱整理成册了。”沈知言把五线谱本摊在桌上,又从包里拿出钢笔,刚要下笔,
就看见林晚秋转身去书架旁,搬了个小梯子,踮着脚往最上层够东西。“你要找什么?
我帮你吧。”沈知言赶紧站起来,走过去扶住梯子,怕她摔下来。
“就是外婆留下的几个铁皮盒,里面装着书签,我想把它们拿下来,整理一下,
有些书签受潮了,想晒晒太阳。”林晚秋指着最上层的几个铁皮盒说,“红色的那个就是,
你帮我拿一下就行。”沈知言点点头,伸手把红色铁皮盒拿下来,盒子有点沉,
上面印着小小的梅花图案,锁扣已经生锈了,轻轻一碰就发出“咔嗒”的轻响。
他把盒子放在桌上,小心地避开林晚秋煮好的粥,
生怕把汤汁洒在盒子上:“这里面都是梧桐叶书签吗?昨天看你书里夹的,都压得很平整。
”“大多是,还有些银杏叶和彩纸折的。”林晚秋搬着梯子放回墙角,走回桌边坐下,
从抽屉里翻出一把小螺丝刀,对着生锈的锁扣轻轻撬了撬,“外婆以前每年秋天都去捡叶子,
回来洗干净、晾干,再压在厚重的旧书里,等过两个月拿出来,就是平整的书签了。
去年她走后,这些盒子就一直放在上层,我还没好好整理过。”螺丝刀撬了两下,
锁扣就开了,林晚秋轻轻掀开盒盖,里面铺着一层浅灰色的绒布,
绒布上整齐地摆着几十张书签——梧桐叶的居多,
金黄的叶片上还能看清细密的脉络;偶尔夹杂着几片银杏叶,像小扇子似的,
边缘有点卷;最底下压着几张彩纸折的小纸船,纸是淡蓝色的,已经有点褪色,
却依旧能看出折痕的工整。沈知言凑过来,伸手轻轻捏起一张梧桐叶书签,指尖碰到叶片,
能感受到干燥的质感,没有一点潮气:“你外婆手真巧,我外婆以前也喜欢做手工,
不过她是织围巾,每年冬天都给我织一条,颜色都是浅色系的,跟我今天穿的这件差不多。
”“是吗?我外婆也会织围巾,去年冬天还织了一条粉色的给我,我现在还戴着。
”林晚秋笑着说,也拿起一张书签,夹进昨天没看完的《城南旧事》里,
“这些书签要是没受潮,以后你抄乐谱累了,想夹书签,就从这里拿,不用客气。
”“那我就不客气了。”沈知言把手里的梧桐叶书签放回盒里,
又帮林晚秋把受潮的书签挑出来,放在窗边的小盘子里,“等会儿太阳出来了,
把这些放在窗台上晒一晒,潮气就能散了,别晒太久,不然叶子会脆得掉渣。
”“我都忘了这点,还好你提醒我。”林晚秋赶紧点头,以前外婆整理书签时,
她总在旁边玩,没记住太多窍门,现在有沈知言帮忙,倒省了不少麻烦。两人吃完早餐,
林晚秋收拾碗筷去厨房洗,沈知言就坐在靠窗的位置,拿出五线谱本开始抄录。
阿橘窝在他脚边,把尾巴绕在他的脚踝上,偶尔抬起头,用爪子轻轻碰一下他垂在腿边的手,
沈知言就会停下笔,摸一摸阿橘的头,动作轻得像怕惊到它。
厨房的水流声、沈知言钢笔的“沙沙”声、阿橘偶尔的“喵”叫声,混在一起,
成了清晨最温柔的声响。林晚秋洗完碗出来,看见这一幕,
忍不住放慢了脚步——暖黄的阳光透过窗户洒进来,落在沈知言的发梢和五线谱本上,
阿橘乖乖地窝在他脚边,书架上的旧书静静立着,整个书店都透着股岁月静好的模样。
她没去打扰,转身回到收银台,拿起那本《钢琴名曲赏析》,轻轻翻开。
昨天沈知言提到他外婆的名字时,她就想再找找,看看书里有没有别的线索。
翻到书的最后几页,她忽然在夹着的一张旧信纸里,看到了一行熟悉的字迹——是外婆的,
写着“清如,下周梧桐巷的桂花开了,咱们一起去捡桂花,做桂花糕吧”。“沈知言,
你快来看!”林晚秋忍不住喊了一声,声音里带着点激动。沈知言立刻停下笔,
走过去:“怎么了?找到什么了?”林晚秋把旧信纸递给他,指着上面的字:“你看,
这是我外婆写的,里面提到了‘清如’,是不是你外婆?”沈知言接过信纸,
指尖轻轻蹭过上面的字迹,眼神瞬间亮了起来:“是!我外婆就叫沈清如,她以前跟我说过,
年轻时住的地方,巷口有棵大桂树,每年秋天都能捡好多桂花做糕!”“真的是!
”林晚秋又翻了翻书,从另一页里找出一张泛黄的照片——照片里有两个年轻姑娘,
都穿着浅粉色的连衣裙,站在一棵桂树下,手里捧着装满桂花的竹篮,笑得格外灿烂。
左边的姑娘眉眼跟外婆很像,右边的姑娘,眉眼竟跟沈知言有几分相似。“这是我外婆!
”沈知言指着右边的姑娘,声音里满是惊喜,“你看,她耳朵上有颗小痣,跟我一样!
”林晚秋凑过去看,果然,右边姑娘的耳垂上有颗小小的黑痣,不仔细看根本发现不了,
而沈知言的耳垂上,也有一颗一模一样的痣。她忍不住笑了:“原来她们真的是闺蜜!
我外婆以前总跟我说,有个闺蜜喜欢钢琴,后来搬去别的地方断了联系,没想到就是你外婆!
”“太巧了,我外婆也跟我说过,有个闺蜜开了家旧书店,喜欢收集梧桐叶书签,
没想到就是你外婆的书店!”沈知言把照片轻轻放在桌上,眼神里满是温柔,
“以前我总觉得,外婆留下的乐谱和书,都是孤零零的,现在才知道,它们还有‘老伙伴’,
就像我找到了你一样。”最后一句话说得很轻,却像羽毛似的,轻轻落在林晚秋的心上,
让她的脸颊瞬间红了。她赶紧低下头,假装整理信纸,小声说:“是啊,太巧了,
说不定这就是外婆们在天上帮我们牵的线。”沈知言看着她泛红的耳根,没再说话,
只是转身回到座位上,重新拿起钢笔,却没立刻抄乐谱——他的心里满是欢喜,
像装了一整个秋天的桂花,甜滋滋的。接下来的几天,沈知言每天都准时来书店。
早上他会带点早餐来,有时是煮好的红薯,有时是刚买的豆浆油条,
有时是自己烤的小面包;林晚秋则会提前煮好粥,或者泡好他爱喝的温水,
放在靠窗的桌子上。吃完早餐,沈知言抄乐谱,林晚秋整理旧书,偶尔谁遇到麻烦,
另一个人就会立刻过来帮忙。有天下午,巷子里来了只流浪狗,对着书店的橱窗狂叫,
吓得阿橘躲在书架后面不敢出来。林晚秋拿着扫帚想把狗赶走,却又有点怕,刚走到门口,
就被沈知言拦在了身后。“我去,你别出来,小心被狗咬到。
”沈知言从店里拿了块剩下的红薯,走到流浪狗面前,把红薯放在地上,轻声哄着,
“别叫了,给你吃的,乖乖的。”流浪狗刚开始还对着他叫,后来闻到红薯的香味,
就慢慢凑过去,叼起红薯躲到旁边吃了起来,没再对着书店叫。沈知言回到店里,
摸了摸躲在书架后的阿橘,轻声说:“别怕,狗走了,以后它再来,我就把它赶走。
”阿橘“喵”了一声,从书架后走出来,跳到沈知言的腿上,窝在他怀里不肯走。
林晚秋看着这一幕,心里暖暖的:“没想到你还会哄狗,我还以为你只懂钢琴和乐谱呢。
”“以前外婆家也养过狗,叫阿黄,我从小跟它一起长大,知道怎么跟狗相处。
”沈知言摸了摸阿橘的头,又看了眼林晚秋,“以后店里要是再遇到这种事,别自己上,
等我来,我比你有力气。”林晚秋点点头,没说话,转身去倒了杯温水递给他——她知道,
沈知言是在护着她,这份藏在小事里的温柔,比任何甜言蜜语都让她心动。
沈知言的乐谱抄得很快,第五天下午,他就把最后一页抄完了。他把抄好的乐谱整理成册,
用黑色的丝带系好,放在桌上,对林晚秋说:“抄完了,明天我把外婆留下的原版乐谱带来,
咱们一起看看,说不定还能找到更多她们俩的线索。”“好啊!”林晚秋眼睛亮了亮,
又有点犹豫地说,“对了,我最近……想学着认五线谱,你要是不忙的话,能不能教我一点?
我想看看外婆留在书里的那些乐谱,到底写的是什么曲子。
”其实她还有句话没说——她想学着认五线谱,是想能跟沈知言有更多共同话题,
想能看懂他抄录的乐谱,想以后他弹曲子时,她能知道他弹的是哪一段旋律。
沈知言愣了一下,随即笑着点头,眼神里满是期待:“当然可以!
明天我带本简单的五线谱入门书来,从最基础的教你,很容易学的,你这么聪明,
肯定一学就会。”“真的吗?那太好了!”林晚秋忍不住笑了,脸颊像沾了蜜似的,
甜得发光。傍晚沈知言走的时候,林晚秋把一张晒干的梧桐叶书签递给他,
书签上用黑色的细笔写了“拾光”两个字,是她下午特意写的:“这个给你,
算是……谢谢你这几天帮我整理书签、赶走流浪狗。以后你弹钢琴,要是想夹书签,
就用这个。”沈知言接过书签,指尖蹭过上面的字迹,心里暖乎乎的:“谢谢,
我会好好收着的,以后每次看到它,就会想起你这家书店,想起你和阿橘。
”看着沈知言的身影消失在巷口,林晚秋回到店里,把他整理好的乐谱册轻轻放在收银台上,
又拿出一本新的笔记本,在扉页上写下“五线谱学习笔记”——她想好好学,
不想让沈知言失望,更想能早日看懂那些藏着外婆和他外婆回忆的乐谱。阿橘凑过来,
趴在她的腿上,“喵”了一声。林晚秋摸了摸阿橘的头,轻声说:“阿橘,你看,
我们的日子是不是越来越热闹了?以后沈知言还会教我认五线谱,说不定以后,
咱们书店里还能听到钢琴声呢。”窗外的梧桐叶又落了几片,铺在门阶上,
暖黄的灯光透过橱窗照出去,把落叶的影子拉得长长的,像在为即将到来的故事,
铺好温柔的底色。第3章 五线谱里的双向试探第二天早上,沈知言比平时早到了十分钟。
他手里拎着帆布包,怀里抱着两本书,一本是五线谱入门书,封面是浅蓝色的,
上面印着大大的音符图案;另一本是棕色封皮的旧册子,封面上没有字,
只有一个小小的铜制搭扣,看起来有些年头了。“这是五线谱入门书,
里面有很多简单的儿歌旋律,学起来不枯燥。”沈知言把浅蓝色的书递到林晚秋手里,
又把棕色的旧册子放在桌上,“这个就是我外婆留下的原版乐谱册,
里面有她和你外婆一起写的曲子,我昨天翻了翻,里面还有她们俩的手写批注。
”林晚秋接过入门书,指尖碰到封面,软软的,很舒服。她又凑过去看那本旧乐谱册,
铜制搭扣上生了点锈,却依旧很有质感:“这就是她们一起写的曲子?我能看看吗?
”“当然能。”沈知言小心地打开搭扣,轻轻掀开册页——里面的纸是泛黄的牛皮纸,
上面用黑色的钢笔写着密密麻麻的音符,偶尔有几处用红笔和蓝笔做的批注,
红笔的字迹娟秀,是沈知言外婆的;蓝笔的字迹温婉,是林晚秋外婆的。
第一页的曲子名叫《巷口桂花香》,开头的音符下面,红笔写着“清如写”,
蓝笔写着“晚卿补”,旁边还画了个小小的桂花图案,可爱又鲜活。林晚秋看着这行字,
眼眶有点湿润——这是外婆和她闺蜜一起写的曲子,时隔这么多年,终于以这样的方式,
重新出现在她眼前。“你看,这里还有她们的约定。”沈知言指着曲子结尾的空白处,
上面写着“待明年桂花开,再补完后半段”,落款是“清如、晚卿,1985年秋”。
“1985年,那时候我外婆才二十多岁。”林晚秋轻声说,指尖轻轻蹭过上面的字迹,
“可惜后来她们断了联系,没能一起补完这首曲子。”“没关系,现在我们找到了,
以后我们可以一起补完。”沈知言看着她,眼神温柔又坚定,“等你学会了认五线谱,
我们就一起研究,把后半段补完,也算圆了她们当年的约定。”林晚秋用力点头:“好!
我们一起补完!”吃完早餐,沈知言就开始教林晚秋认五线谱。他把入门书摊在桌上,
用钢笔指着五线谱的线和间,轻声说:“五线谱有五条线、四个间,从下往上数,
分别是第一线到第五线,第一间到第四间,音符放在不同的位置,代表的音高不一样,
你先记住这个口诀:第一线mi、第二线sol、第三线si……”林晚秋认真地听着,
手里拿着笔,在笔记本上一笔一划地记着口诀,偶尔没记住,就皱着眉问沈知言,
沈知言也不着急,耐心地一遍遍地教她,直到她记住为止。阿橘窝在两人中间的桌子底下,
偶尔抬起头,用爪子轻轻碰一下他们的手,像是在提醒他们别学太久,要休息一会儿。
沈知言教了半个多小时,就停下笔,给林晚秋倒了杯温水:“先休息会儿,别太累了,
五线谱要慢慢学,急不得。”“我觉得挺有意思的,一点都不累。”林晚秋喝了口温水,
又拿出笔记本,指着上面记的口诀,“你再考我一遍,我肯定能记住。”沈知言笑着点头,
随口问了几个音符的位置,林晚秋都准确地答了出来。“你看,我就说你聪明吧,一学就会。
”沈知言忍不住夸她,眼神里满是欣赏。被他这么一夸,林晚秋的脸颊瞬间红了,
赶紧低下头,假装翻入门书,小声说:“都是你教得好,要是换别人教,我肯定学不会。
”两人休息了十分钟,又继续学。这次沈知言教她认简单的节奏,用手轻轻拍着桌子打节拍,
林晚秋也跟着学,刚开始拍得乱七八糟,后来慢慢找到了节奏,能跟上沈知言的节拍了。
“你看,这就学会了。”沈知言停下拍手的动作,笑着说,“以后每天早上我教你半小时,
下午你要是有时间,就自己复习复习,不出一个月,你就能看懂简单的曲子了。”“真的吗?
那太好了!”林晚秋眼睛亮了亮,心里满是期待——她想快点学会,
想快点看懂《巷口桂花香》,想快点跟沈知言一起补完这首曲子。接下来的日子,
书店里每天早上都会响起沈知言教五线谱的声音。林晚秋学得很认真,每天下午关店后,
都会留在店里复习,把沈知言教的内容再看一遍,对着入门书里的简单曲子,
一点点地认音符、打节拍。有时候遇到不懂的,她就记在笔记本上,第二天早上问沈知言。
沈知言也很有耐心,不管她问多少遍,都耐心地解答,
偶尔还会用钢笔在她的笔记本上画小小的音符,帮她加深记忆。
有次林晚秋把“sol”和“la”记混了,沈知言就用钢笔在她的笔记本上画了个小太阳,
旁边写着“sol像小太阳,在第二线”,林晚秋看着这个小太阳,一下子就记住了,
再也没弄混过。中途林晚秋也想过放弃——有次遇到一段节奏复杂的曲子,
她认了半天都没认对,还把节拍打得乱七八糟,心里有点失落,把笔往桌上一放,
小声说:“怎么这么难啊,我好像学不会了。”沈知言赶紧走过去,拿起她的笔记本,
轻轻摸了摸她的头:“不难不难,是这段曲子有点复杂,我们先跳过,学简单的,
等你熟练了,再回来学这段。你已经很棒了,才学了两周,就能看懂《小星星》的谱子了,
比我当初学得快多了。”说着,他从帆布包里拿出手机,打开一个音频文件,
点了播放——手机里传来轻柔的钢琴声,是《小星星》的旋律,节奏舒缓,音色温柔。
“你听,这是我昨天弹的《小星星》,等你学会了,我就弹给你听,好不好?
”林晚秋听着钢琴声,心里的失落渐渐散去,她点点头,重新拿起笔:“好,我不放弃,
我接着学。”沈知言看着她重新振作起来的模样,
嘴角忍不住上扬——他喜欢看林晚秋认真的样子,喜欢看她为了一个目标努力的样子,
更喜欢看她因为学会了一个知识点,而笑得眼睛亮晶晶的样子。
其实沈知言也有自己的小心思。他每天早上教林晚秋五线谱,
不仅仅是想帮她圆“看懂外婆乐谱”的心愿,更是想找个理由,能每天多待在书店里,
多看看她,多跟她待一会儿。有天下午,林晚秋整理书架时,
从一本旧书里翻出了一张未完成的钢琴曲谱,纸页泛黄,边角有点破损,
上面的音符只写了前半段,结尾处画了个小小的问号,
旁边还有外婆的蓝笔批注:“等清如回来,一起补完。”她赶紧把谱子收好,
等沈知言第二天来书店时,小心翼翼地递给他:“沈知言,你看,我从旧书里翻出了这个,
是我外婆写的,好像是跟你外婆没补完的另一首曲子。”沈知言接过谱子,
指尖轻轻抚平破损的边角,认真地看着上面的音符,越看眼睛越亮:“这曲子的旋律,
跟我外婆乐谱册里的一首《梧桐叶落时》能接上!你看,这里的收尾音,
刚好能跟《梧桐叶落时》的开头对上!”说着,他从帆布包里拿出外婆的乐谱册,
翻开其中一页,把两张谱子放在一起——果然,林晚秋外婆写的谱子收尾音是“la”,
而沈知言外婆的《梧桐叶落时》开头音也是“la”,旋律衔接得自然又流畅,
像是原本就是一首完整的曲子。“太好了!”林晚秋忍不住拍手,
“这样我们就有两首没补完的曲子了,等我学会了五线谱,我们就一起把它们都补完,
圆了外婆们的约定!”“嗯,一起补完。”沈知言看着她雀跃的模样,心里软乎乎的,
“等补完了,我就弹给你听,弹给外婆们听。”林晚秋点点头,脸颊有点红,小声说:“好,
我等着听。”为了能早点看懂这些谱子,林晚秋学得更认真了。每天关店后,
她都会留在店里,对着谱子一点点认音符,有时候认到天黑,就打开台灯,继续学。
有次沈知言晚上路过书店,看见橱窗里亮着的台灯,还有里面林晚秋认真的身影,
忍不住走过去,敲了敲橱窗。林晚秋抬头,看见是他,赶紧走过去开门:“你怎么来了?
这么晚了还没休息吗?”“路过,看见你店里还亮着灯,就过来看看。”沈知言走进店里,
看见桌上摊开的谱子和写满笔记的笔记本,心里有点心疼,“怎么学这么晚?别累着眼睛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