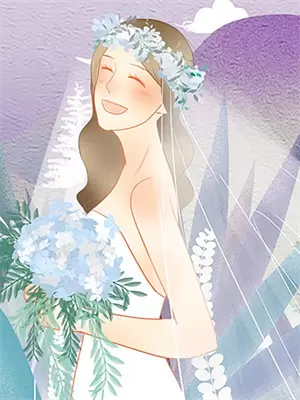
意识恢复的时候,我正飘在半空中,像一粒微不足道的尘埃。
下方,是我自己的葬礼。
灵堂布置得很简单,甚至有些仓促。正中央挂着我那张永远停留在二十七岁的、显得有些过分严肃的黑白照片。照片里的我,眼神是我自己都陌生的茫然,仿佛早就预知了此地的冷清。
来的人不多,稀稀拉拉坐了几排。
我的父母坐在最前面,母亲王芳的眼睛是肿的,但那更像是熬夜的疲惫,而非悲伤的痕迹。父亲江建军则板着脸,眉头紧锁,像是在出席一个让他感到难堪的会议。
我的几个“朋友”也来了。为首的是张伟,我大学时的室友。他穿着一身不合身的黑西装,脸上带着一种社交式的、恰到好处的沉痛。他身边的人,我甚至叫不出名字,大约是觉得这种场合,一个人来会显得过于尴尬吧。
我飘过去,想拍拍父亲的肩膀,告诉他别皱眉了,我这个“没出息”的儿子,终于不会再给他丢脸了。但我的手,径直穿过了他的身体,带不起一丝涟漪。
原来,我真的死了。
死于一场雨夜的交通事故。一辆失控的卡车,结束了我这短暂又乏善可陈的一生。
也好。
活着的时候,我总觉得自己像个多余的人,融不进这个世界。现在,我以一种更彻底的方式,被世界排斥在外了。
哀乐低回,主持人用一种毫无感情的语调,念着我的生平。
“江离,生于……毕业于……一生平凡,为人内向……”
很短,也很客观。客观得像一份产品说明书,冰冷,精准。
我看见母亲低下头,用手帕捂住了脸。我以为她终于要哭了,飘近一看,才发现她只是在打一个长长的哈欠。
父亲则掏出手机,在桌子底下,回复着一条工作信息。
朋友那桌,张伟正低声和旁边的人说着什么。
我好奇地凑过去。
“……真是,太突然了。上周还说一起吃饭的。”张伟叹了口气。
“他这人就这样,神神叨叨的,平时也不出来玩。”另一个人说,“听说,工作也一直不顺心?”
“嗨,别提了。眼高手低,总想搞些不切实际的东西。我劝过他好几次,让他现实点,他不听。”张伟摇摇头,语气里带着一丝“我早就说过”的优越感。
看吧,这就是我的朋友。
在我的葬礼上,他们还在给我下着最终的、盖棺定论的判词。
我没有等到林珂。
那个我爱了整整七年,却最终选择了一个“更正常、更上进”的男人的女孩。
她没有来。
也好。我不想让她看见我这最后的不体面。
整个仪式,不到半个小时就结束了。
没有人哭。
没有撕心裂肺的悲痛,没有依依不舍的留恋。
就像一阵风吹过,把地上一片无关紧要的落叶,吹走了。仅此而已。
宾客们陆续散去,脸上那种程式化的悲伤,像面具一样被迅速摘下,换上了属于人间的、鲜活的表情。
他们讨论着待会儿去哪里吃饭,讨论着最近的股票,讨论着孩子的升学。
我的死亡,不过是他们庸常生活里,一个微不足道的插曲。
最后,只剩下我的父母,和殡仪馆的工作人员。
“江先生,江太太,这边请,我们来谈一下火化的费用。”
我飘在空中,看着父母跟着工作人员,走向那个亮着“缴费处”灯牌的房间。
我忽然觉得,这一幕,比我的死亡本身,还要荒诞。
我,江离,活了二十七年。
不被理解,不被喜爱,不被需要。
死后,连一场像样的、带着真诚泪水的告别,都得不到。
我飘荡在空旷的灵堂里,看着照片里那个陌生的自己。
一股比活着时,强烈千百倍的孤独感,将我紧紧包裹。
就像沉入了冰冷的海底,四周是无尽的黑暗和死寂,听不见一丝声音,看不见一缕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