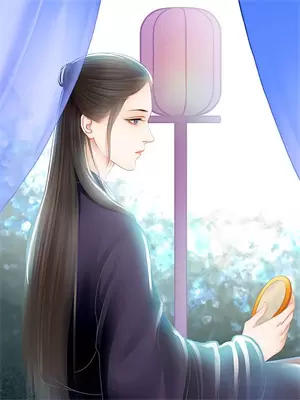绝对的灰暗。不是夜晚的黑,而是色彩的彻底死亡,是连光线本身都被吞噬的虚无。
长途汽车的引擎发出濒死的呜咽,车灯早已熄灭,我们像一枚被投入墨汁的锈铁钉,
在粘稠的、令人窒息的黑暗中盲目前行。唯一的坐标,是视野尽头,
那个微弱、摇曳、却固执存在的乳白色光点。它太遥远了,像宇宙诞生之初的第一缕星芒,
渺小得几乎要被周围的虚无碾碎。但它存在着,这本身就是一个违背了当前世界规则的奇迹。
它周围的灰暗,似乎真的……淡了那么一丝丝?像一滴清水滴入了浓墨,虽然微不足道,
却划出了一道清晰的界限。司机像抓住了最后的救命稻草,双手死死攥着方向盘,
眼睛瞪得几乎要裂开,死死“锁定”着那个光点,
尽管它大部分时间都隐没在翻涌的灰色潮汐之后。老太太蜷缩在座位下,
发出断续的、如同风中残烛般的祈祷。而我,靠在冰冷的车窗上,
感觉自己的体温正一点点被抽离,意识在冰冷和麻木的边缘沉浮。
那光点是我残存意识的锚点,每一次它从灰暗中挣扎着显现,都像一次微弱的心跳,
提醒我还“存在”。不知过了多久,时间在这里失去了意义。也许是一分钟,
也许是一个世纪。汽车的速度慢了下来,发动机的咆哮变成了苟延残喘的喘息。
前方的灰暗似乎……稀薄了一些?不再是那种吞噬一切的浓稠,而是变成了……雾?
一种灰色的、冰冷的、带着浓烈墙灰和腐朽气息的浓雾。能见度稍微提高了一点,
但眼前的景象更令人绝望。我们似乎驶入了一片“过渡区”。公路还在,
但路面已经彻底变成了灰白色,像被漂白过,又像是覆盖了一层厚厚的骨灰。
旁的景象更是骇人——树木、房屋、废弃的车辆……所有的一切都失去了原本的形态和色彩,
变成了扭曲的、灰白色的、如同融化后又凝固的蜡像般的怪异雕塑。
它们静静地矗立在浓雾中,轮廓模糊,散发着死寂的气息。这里仿佛经历过一场无声的核爆,
所有物质的结构和色彩都被瞬间抹除,只留下这惨白的、如同噩梦般的残骸。而那个光点,
似乎近了一些。它就在这片惨白废墟的深处。司机猛踩油门,汽车发出最后一声嘶吼,
冲破了最后一片浓雾。瞬间,我们冲入了一片……相对“正常”的区域。
就像穿过了一层看不见的薄膜。虽然天空依旧是铅灰色的,压抑得让人喘不过气,
空气中依然弥漫着那股熟悉的腐朽味,但浓度明显降低了。更重要的是,色彩回来了!
虽然像是蒙着一层厚厚的灰尘,黯淡无光——土地是灰褐色的,
远处残破的建筑是暗沉的水泥色,零星几棵顽强存活的树木,
叶子是病恹恹的黄绿色——但至少,它们不再是那种绝对的、令人疯狂的灰白!
我们冲出了最核心的“死亡区”!汽车彻底熄火了,滑行了一段距离后,
停在了这片“灰色世界中的绿洲”边缘。司机瘫在方向盘上,大口喘着粗气,
浑身被冷汗湿透。座位下的老太太也停止了祈祷,茫然地抬起头。我推开车门,
脚踩在灰褐色的、略显松软的土地上。一种虚脱感袭来,但我强迫自己站直,环顾四周。
这里像是一个废弃的工业区边缘,到处是破败的厂房和堆积的废弃物。远处,
可以看到一些低矮的建筑轮廓,似乎还有微弱的灯火?不,不是灯火,是……烛火?
或者是某种更原始的、摇曳不定的光源。而那个引导我们前来的乳白色光点,
此刻清晰地悬浮在前方几百米外的一座……看起来像是废弃教堂或者仓库的尖顶建筑上方。
光芒柔和而稳定,像一盏指引迷途灵魂的孤灯。这里有人?还有抵抗的力量?
这个发现让我死寂的心湖泛起一丝波澜。我们不是唯一的幸存者?
我搀扶着几乎虚脱的司机和惊魂未定的老太太,
朝着那座发出光亮的建筑深一脚浅一脚地走去。越靠近,越能感受到一种奇异的“场”。
不是温暖,而是一种……秩序感?仿佛有一种无形的力量,
在努力维持着这片区域的“正常”,抵抗着外部灰暗的侵蚀。
空气中的腐朽味在这里也淡了许多,虽然依旧令人不适。我们走到建筑前。
这是一座用粗糙巨石垒砌的、带有明显哥特式风格的古老小教堂,但显然已经废弃多年,
窗户破损,墙壁上爬满了枯死的藤蔓。然而,教堂那扇厚重的木门却紧闭着,
门缝里透出微弱的光。而那个乳白色的光点,
正是从教堂尖顶上一个小小的、像是玻璃制成的结构物中散发出来的。我深吸一口气,
抬手敲响了木门。敲门声在死寂的环境中显得格外响亮。门内传来细微的响动,
然后是门闩被拉开的沉重声音。木门吱呀一声,打开了一条缝隙。
一张布满皱纹、写满疲惫和警惕的老人的脸,从门缝后探了出来。他的眼睛在昏暗的光线下,
闪烁着一种……难以形容的、混合着智慧和深深倦怠的光芒。
他的目光扫过我们三个狼狈不堪的幸存者,最后落在我身上时,微微停顿了一下,
眉头不易察觉地皱起。“外面来的?”他的声音沙哑,带着一种长期缺乏交流的干涩。
我点点头,喉咙发紧,一时不知该说什么。老人又仔细打量了我们一番,
特别是多看了我几眼,眼神中闪过一丝极其复杂的情绪——有惊讶,有怜悯,
还有一丝……深深的忧虑?他最终叹了口气,侧身让开了通道。“进来吧。”他说道,
声音里带着一种认命般的疲惫,“虽然……这里也撑不了多久了。
”我们三人踉跄着走进教堂。门在身后沉重地关上,将外面那个灰暗死寂的世界暂时隔绝。
教堂内部比外面看起来要完整一些,虽然同样破败,布满灰尘,
但中央点燃着几根粗大的、散发着奇异清香的蜡烛,提供了主要的光源。烛光摇曳,
映照出教堂尽头残破的圣像,以及分散坐在长椅上的、大约二三十个身影。有男有女,
有老有少,每个人都面黄肌瘦,衣衫褴褛,脸上带着深深的疲惫和麻木,但他们的眼神深处,
还残存着一丝微弱的光,那是求生的本能,或许……还有一丝信仰?他们看到我们进来,
只是麻木地抬了抬眼皮,没有任何反应,仿佛已经习惯了这种偶尔有幸存者闯入的情形。
带领我们进来的老人,是这里看起来最有精神的一个,
也是唯一一个眼神中还保留着清醒思考能力的人。他指了指角落一堆还算干净的干草,
“坐吧。这里有点吃的和水,不多,省着点。”我扶着司机和老太太坐下,自己却无法平静。
我走到老人身边,急切地低声问:“老人家,这里是什么地方?外面……到底发生了什么?
那个光……”老人抬起浑浊的眼睛,看着我,又看了看教堂尖顶的方向,苦涩地笑了笑。
“这里?是‘守夜人’最后的哨所之一。至于发生了什么……”他顿了顿,声音低沉下去,
“用你们能理解的话说……‘现实’正在被‘覆盖’。就像……一张画布,
正在被另一种颜色重新涂抹。”他的目光再次落在我身上,带着一种穿透灵魂的锐利。
“而你,年轻人……”他缓缓说道,每一个字都像沉重的石头砸在我心上,
“你身上带着‘门’那边的气息……很浓,非常浓。你不是普通的幸存者。
你……是从‘风暴眼’里出来的,对吗?”我的心猛地一沉。守夜人?风暴眼?
他……知道锦华苑?!他知道那口“井”!我看着他,
看着这座在灰色废墟中顽强亮着微光的破败教堂,看着那些麻木的幸存者。我终于明白,
那引导我们前来的光,不是希望之光。那是……最后的烽火。而我的到来,
对于这座最后的堡垒而言,或许并非福音。我带来的,可能是……加速其毁灭的……灾厄。
老人浑浊的眼睛像两口干涸的深井,倒映着摇曳的烛光,也倒映着我脸上无法掩饰的惊骇。
他看穿了我。他不仅知道灾难,还知道锦华苑,知道那口“井”,
甚至能嗅出我身上来自“风暴眼”的、洗刷不掉的污秽气息。
“守夜人……最后的哨所……”我重复着这个词,声音干涩得像是砂纸摩擦。
教堂里昏暗的光线,幸存者们麻木的脸,空气中那股混合着烛火清香和外界腐朽气息的味道,
都让这一切显得如此不真实,却又如此沉重。老人,他自称老葛,
示意我跟他走到教堂一侧稍微僻静的角落。他佝偻着背,步伐缓慢,
每一步都带着深深的疲惫。“守夜人,是很久以前的称呼了。
”老葛靠在一张积满灰尘的诵经台边,声音低沉,“祖辈传下来的说法。说这个世界,
不只有我们看到的一面。有些地方,是‘薄’的,像窗户纸,容易……被不该来的东西捅破。
还有些东西,一直就在下面,睡着,或者被关着。守夜人的职责,就是看着这些地方,
守着那些封印,不让平衡被打破。”他抬起枯瘦的手指,指了指教堂尖顶的方向,
那乳白色的光正是从那里发出。“那‘引路烛’,是老祖宗留下的最后一点东西了。
用特殊的方法点燃,能……在一定程度上,驱散‘虚妄’,照亮一小片真实的边界,
暂时抵挡‘覆盖’。”“覆盖……”我捕捉到这个关键词,心脏抽搐了一下。“嗯,覆盖。
”老葛的眼神飘向紧闭的大门,仿佛能穿透厚实的木板,看到外面那个正在死去的世界,
“就像你说的那口‘井’,它就是个窟窿,一个……门。门开了,
门后面的‘颜色’……就开始漫出来,涂改我们这个世界。先是离得近的,然后越来越远。
颜色没了,声音没了,温度没了……最后,连‘存在’本身,都会被抹掉,变成……‘无’。
”他的描述精准得可怕,印证了我所有的恐怖经历。这不是物理毁灭,
而是规则层面的侵蚀和同化!“那……‘祂’呢?”我颤声问出最恐惧的问题。
老葛的身体几不可察地抖了一下,他深深地看着我,眼神里充满了难以言喻的复杂情绪,
有恐惧,有敬畏,还有一种……近乎绝望的宿命感。“‘祂’……是门后面的‘主人’之一。
或者说,是那种‘颜色’本身。我们无法理解‘祂’是什么,
就像画布上的颜料无法理解画家的意志。我们只知道,当‘祂’的颜色覆盖一切时,
我们的世界……就没了。”“没有办法阻止吗?封印回去?或者……消灭‘祂’?
”我急切地问,尽管知道希望渺茫。老葛惨然一笑,摇了摇头,脸上的皱纹像干涸的河床。
“封印?钥匙已经丢了。至于消灭……”他像是听到了最可笑的笑话,“蝼蚁,
能消灭洪水吗?我们能做的,只是尽量延长被淹没的时间。像这座教堂,像这盏‘引路烛’,
就像洪水中的一个小小气泡,暂时隔开洪水,但气泡……迟早会破的。”他顿了顿,
目光再次锐利地聚焦在我身上:“尤其是……当气泡里,
混进了一滴特别‘浓’的洪水的时候。”我明白他的意思。我就是那滴“浓水”。
我从风暴眼中心出来,身上带着“祂”最本源的气息。我的存在本身,
就像在油锅里滴入冷水,会急剧加速这个“气泡”的破裂。
“对不起……我……”我喉咙发紧,愧疚和无力感几乎将我淹没。老葛摆了摆手,打断了我,
眼神中的锐利被一种深沉的疲惫取代。“不怪你。孩子,这是命数。平衡早就千疮百孔了,
没有你,气泡也撑不了多久。你的到来,或许……也是一种必然。”他叹了口气,
望向那些麻木的幸存者:“我们能做的,就是在这最后的时间里,尽量多救几个人,
尽量……让更多的人,在清醒中面对终结,而不是在浑浑噩噩中被抹去。
”“终结……什么时候会来?”我声音发颤。老葛抬头看了看尖顶的光芒,
那光芒似乎比刚才又微弱了一丝。“‘引路烛’的火苗越来越弱了。当它熄灭的时候,
就是这座教堂,和我们所有人,被彻底‘覆盖’的时候。快则一两天,慢则三五日。
外面的‘灰色’……已经离得很近了。”一两天?三五日?这个倒计时像最后的丧钟,
在我脑中轰鸣。我原本以为自己找到了一丝喘息之地,没想到却是直接踏入了最后的审判庭。
“就没有……任何别的办法了吗?”我不甘心地追问,哪怕是一线虚无缥缈的希望。
老葛沉默了很久,久到我以为他不会回答了。最后,
他用一种极其轻微、仿佛怕被什么存在听到的声音,
近乎耳语般说道:“古老的记载里……有过一个猜测。只是猜测,从未证实过,
也无人敢尝试。”“什么猜测?”我屏住呼吸。“据说……如果有一个灵魂,
其‘念’足够强大,足够特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