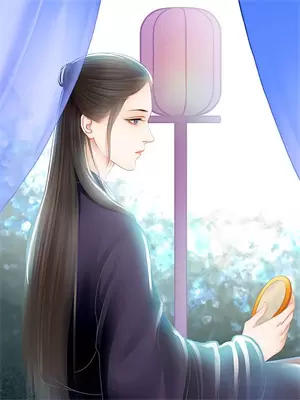1 阴雨天的来客雨丝斜斜地织在青石板路上,把整条老街洇成了墨色。
林瞎子收起最后一张黄纸符,指尖在潮湿的木桌上捻了捻,
鼻腔里涌入樟树与霉味混合的气息。他这铺子开在城隍庙后墙第三间,
门楣上挂着块褪了色的木匾,"乾坤堂"三个字被雨水泡得发胀,
倒像是随时会从木板上渗出来。"吱呀"一声,挂着铜铃的木门被推开。林瞎子耳朵动了动,
不是熟客拖沓的脚步声,来人鞋底沾着沙砾,踩在青砖上带着细碎的刮擦声,
更像是从城外工地上来的。"先生,算命。"男人声音发紧,带着被雨呛过的沙哑。
林瞎子摸索着把紫砂壶往桌边推了推:"报生辰。
"他指尖在桌面上那道深痕上轻轻敲着——那是十年前被一把匕首划下的,
当时血珠滴在卦盘上,把乾位的纹路染成了紫黑色。"光绪三十四年,三月初七,寅时。
"男人报完忽然顿住,"先生...能算生死吗?"林瞎子指尖在龟甲上停住。
这生辰他太熟了,去年今日,也是这样一个阴雨天,城南绸缎庄的王掌柜就坐在这张椅子上,
报的同样生辰。王掌柜算出自己活不过中秋,当场给了双倍卦金,只求破法。
林瞎子没收那钱,只说命数天定。结果中秋刚过三天,就传来王掌柜在自家库房上吊的消息,
舌头伸得老长,脚尖离地面还有半尺。"生死有命。"林瞎子把龟甲往桌上一扣,
"卦金二十文,不算阳寿。"男人忽然从怀里掏出个油纸包,"哗啦"一声倒在桌上。
碎银滚得满桌都是,其中一块还撞在林瞎子的茶碗上,发出清脆的响。"我给十倍。
"男人声音发颤,"我就想知道,我那兄弟...还有没有救。"林瞎子的鼻尖动了动。
这男人身上除了雨水味,还有股淡淡的血腥味,藏在腋下的位置,像是用什么东西捂着。
他缓缓伸出手,指尖先摸到男人的手腕,脉搏跳得又急又乱,虎口处有层厚茧,
是常年握刀的人才有的。"八字。"林瞎子的声音沉了沉。"同治十一年,腊月初九,酉时。
"男人说得飞快,"他叫赵大奎,昨天去黑风口拉货,到现在还没回来。"林瞎子摸到龟甲,
指尖捻起三枚铜钱。铜钱边缘磨得发亮,是他师父传下来的,
据说浸过七七四十九个死刑犯的血。他把铜钱扣在掌心晃了晃,刚要掷出去,
忽然听见门外传来急促的脚步声,伴随着铜铃的剧烈晃动。"林先生!林先生!
"捕头张彪的大嗓门撞进门来,带着一身酒气和雨腥,"城南发现个死人,你去看看!
"林瞎子没动。他听出张彪脚步声里的虚浮,这醉鬼捕头平时八抬大轿都请不动,
今天主动上门,必是出了大事。"死人归官府管。"林瞎子把铜钱放回龟甲里,
"我这是算命的铺子,不是仵作房。""不一样!"张彪一把抓住林瞎子的胳膊,
他手心烫得吓人,"那死人...脸上被人画了符!跟去年王掌柜脸上的一模一样!
"桌上的男人突然"啊"地叫了一声,身子猛地往后缩,椅子腿在地上划出刺耳的声。
林瞎子耳朵微微一动,听见他牙齿打颤的声音,像秋风里的落叶。"你认识死者?
"张彪的声音陡然严厉起来。男人喉咙里发出嗬嗬的响声,半天说不出话。林瞎子摸到茶碗,
呷了口已经凉透的茶,茶梗在舌尖涩得发苦。他想起王掌柜死时的模样,张彪当时也在场,
吓得差点摔了手里的酒壶——死者额头用朱砂画着个歪歪扭扭的"乾"卦,
血珠沿着纹路渗进皮肉里,像是从骨头里长出来的。"去看看吧。"林瞎子站起身,
摸索着拿起墙角的竹杖。竹杖底端包着铁皮,敲在青石板上发出笃笃的响,"在哪发现的?
""黑风口的老槐树下。"张彪的声音低了下去,"跟赵大奎拉货的路线...正好顺路。
"桌上的男人突然瘫在地上,发出重物落地的闷响。林瞎子听见他裤裆里传来水声,
一股骚臭味混着雨水味漫开来。"他...他就是赵大奎的同伙,李老四。
"张彪踢了男人一脚,"刚才还跟你打听赵大奎的死活?"林瞎子的竹杖在门槛上顿了顿。
雨还在下,城隍庙的铜钟声从雨幕里钻过来,敲了三下。
他忽然想起师父临终前说的话:"瞎子算命,算的不是命,是人心。人心比鬼可怕,
尤其是沾了血的人心。"黑风口的老槐树有百年了,枝桠像鬼爪似的抓着阴沉的天。
林瞎子刚走到树下就停住脚,竹杖尖在泥地里轻轻点着。空气中除了泥土和腐叶的腥气,
还有股熟悉的甜腻味,跟王掌柜死时库房里的味道一样,是用苏木和辰砂混合的气味,
画符专用。"先生你看。"张彪的声音发紧,"这额头..."林瞎子蹲下身,
指尖先摸到死者的脸。皮肤已经凉透了,额头的皮肤被什么东西划破,结成硬痂,
形状正是乾卦的六爻。他顺着脸颊往下摸,摸到死者的下巴时突然停住——下巴上有颗痣,
绿豆大小,跟李老四描述的赵大奎一模一样。"死了多久?"林瞎子问。
"仵作说...至少十二个时辰了。"张彪的声音离得老远,像是不敢靠近,"奇怪的是,
身上没伤,就额头这道符,像是...自己长出来的。"林瞎子没说话。他摸到死者的手腕,
骨头是断的,却不是新伤,断面已经长了层薄骨痂。再往下摸,手心空空的,
指甲缝里全是泥,唯独右手无名指的指甲缺了一块,边缘还留着新鲜的血迹。
"他手上少了什么?"林瞎子问。张彪凑过来打了个喷嚏:"不知道啊,发现的时候就这样。
哦对了,李老四说赵大奎手上总戴着个银镯子,是他娘给的,保命用的。
"林瞎子的指尖在死者无名指的缺口处停住。这缺口很整齐,像是被人用刀削掉的。
他忽然想起什么,摸向死者的领口,果然在夹层里摸到个硬纸包,拆开一看,是半张黄纸,
上面用朱砂画着半道符,墨迹还没干透。"把李老四带过来。"林瞎子站起身,
竹杖在地上敲出急促的点,"我有话问他。"雨越下越大,打在槐树叶上沙沙作响。
张彪押着李老四过来的时候,那男人已经吓得站不住了,两条腿抖得像筛糠。
林瞎子听见他裤脚滴水的声音,混着地上的血水,在泥地里晕开一小片深色。
"赵大奎的银镯子呢?"林瞎子问。李老四"扑通"跪在地上:"我不知道!真不知道!
昨天我们分道走的,他说去会个朋友,让我先回...我以为他早到家了啊!""什么朋友?
""不...不知道..."李老四的声音越来越小,
"他就说...是个算命的..."林瞎子的竹杖猛地顿在地上,铁皮撞在石头上,
发出刺耳的响。雨幕里突然传来一阵铃铛声,远远的,像是有人在摇招魂铃。
他抬头望向槐树深处,那里的雾气浓得化不开,仿佛藏着无数双眼睛,正幽幽地盯着他们。
张彪突然"啊"了一声,指着死者的手:"先生你看!他手里...好像攥着东西!
"林瞎子赶紧蹲下身,掰开死者僵硬的手指。指缝里是些潮湿的木屑,还有一小块碎布,
蓝底白花,摸着像是绸缎庄的料子。他把碎布凑到鼻尖闻了闻,除了霉味,
还有股淡淡的脂粉香,是去年王掌柜店里卖得最火的那款"醉春楼"的香粉。
"王掌柜的绸缎庄,"林瞎子的声音冷得像冰,"去年是不是丢过一批蓝底白花的绸缎?
"张彪愣了愣:"好像是有这么回事!当时王掌柜还报了官,说是被偷了十匹,
价值连城..."林瞎子站起身,竹杖指向县城的方向。雨雾中,城隍庙的金顶若隐若现,
像颗沉在水底的珠子。"去绸缎庄。"他说,"这符,不是画给死人的,是画给活人的。
"2 绸缎庄的秘闻绸缎庄的门板卸到第三块时,林瞎子听见了哭声。是个女人的声音,
压得很低,像被什么东西捂着,从后堂飘过来,混着檀香味和丝绸的气息。"王夫人。
"张彪的声音放得很轻,"我们来问问去年失窃的事。"哭声停了。过了半晌,
一个穿着素色旗袍的女人走出来,脚步声踩在地板上几乎听不见。林瞎子的鼻尖动了动,
她身上除了丧服的浆味,
还有股熟悉的香粉味——正是赵大奎指缝里那块碎布上的"醉春楼"。"张捕头想问什么?
"女人的声音发哑,像是很久没说过话。"去年丢的绸缎,"林瞎子接过话头,
"是蓝底白花的吗?"女人沉默了片刻:"是。那批料子是从苏杭运来的,
上面的缠枝莲是用金线绣的,全县城只我家有。""丢了多少?""十匹整。
"女人的声音突然抖了一下,"当时查了很久,没找到...我家老爷为此气病了好几天。
"林瞎子的指尖在竹杖上摩挲着。王掌柜死在中秋,而绸缎失窃是在清明,中间隔了半年。
这半年里,王掌柜到底在怕什么?他忽然想起王掌柜算卦那天,手里攥着块蓝布,
指节捏得发白,像是攥着什么烫手的东西。"王掌柜死前,"林瞎子缓缓开口,
"有没有提过黑风口?"女人突然"啊"地一声,后退半步撞在门框上,发出"咚"的闷响。
"你怎么知道..."她的声音里带着惊恐,"他...他死前三天,确实去过黑风口,
说去收账。""收谁的账?""不认识的人..."女人的声音越来越低,
"他说对方给的价钱很高,要现金交易。我劝他别去,那地方不安全,
可他不听..."林瞎子转向张彪:"查下去年清明到中秋,所有在黑风口附近失踪的人。
"他的竹杖在地板上敲了敲,"尤其是手上戴银镯子的。"张彪刚要应声,
后堂突然传来"哐当"一声,像是有什么东西摔碎了。女人脸色一白,拔腿就往后跑。
林瞎子听见她踩在碎瓷片上的声音,还有个男人压抑的咳嗽声,从后堂深处传来。
"里面还有人?"张彪拔出手铐,哗啦一声响。女人慌忙拦在门口:"没...没有!
是我家下人不小心打碎了东西!"林瞎子却已经摸到了后堂的门。门是虚掩着的,他推开门,
一股浓重的草药味扑面而来,混着淡淡的血腥气。他的竹杖往前探了探,触到一个人的膝盖,
那人猛地一颤,发出"嘶"的抽气声。"先生..."那人的声音很轻,带着伤后的虚弱,
"别告诉别人我在这..."林瞎子的指尖摸到那人的手腕,脉搏跳得很慢,
虎口处有层薄茧,跟赵大奎的很像。他再往上摸,摸到下巴,那里光溜溜的,没有痣。
"你是谁?"林瞎子问。"我..."那人顿了顿,"我是王掌柜的远房侄子,来投奔他的。
"林瞎子的竹杖突然往下一沉,触到地上的一个东西。是个银镯子,
上面刻着"长命百岁"四个字,边缘有处缺口,像是被硬物砸过。"这镯子是谁的?
"林瞎子把镯子踢到张彪脚边。张彪捡起镯子对着光看了看:"这...这是赵大奎的!
李老四认得这缺口!"后堂里突然安静下来,只有窗外的雨声和那人急促的呼吸声。
林瞎子听见女人牙齿打颤的声音,还有那人悄悄往墙角挪动的响动,像是想找地方躲。
"赵大奎是你杀的?"张彪的声音陡然严厉。"不是我!"那人突然叫起来,
"是他自己找死!他拿着那批绸缎要挟我姑丈,说要去报官...""什么绸缎?
"林瞎子追问。"就是去年丢的那批..."那人的声音低了下去,"其实不是被偷了,
是我姑丈偷偷卖给黑风口的土匪,
换了鸦片..."女人突然哭出声:"是真的...我家老爷沾了大烟后,性情大变,
把家底都快败光了。那批绸缎是他最后的指望,结果被赵大奎和李老四劫了,
他们逼着老爷拿鸦片换,不然就去报官..."林瞎子的竹杖在地上画着圈。
王掌柜额头的乾卦,赵大奎指缝里的碎布,
还有这突然冒出来的侄子...事情好像串起来了,又好像缺了最重要的一环。
"王掌柜是怎么死的?"林瞎子问。女人的哭声顿住了:"他...他是被土匪逼死的。
赵大奎把绸缎卖给土匪后,土匪嫌料子有问题,说是被掉了包,就杀了王掌柜泄愤,
还画了那鬼符...""那你侄子手上的伤是怎么回事?"林瞎子的声音冷得像冰。
女人突然没了声音。林瞎子听见那人往门口挪动的声音,脚步声很轻,像是想趁机溜走。
他猛地把竹杖往前一探,正戳在那人的膝盖窝,那人"哎哟"一声跪了下来,
发出沉重的响声。"他手上的伤,"林瞎子的指尖摸到那人的右手,
无名指的指甲果然缺了一块,边缘还缠着带血的布条,"是跟赵大奎搏斗时弄的吧?
"那人突然大笑起来,笑声里带着疯狂:"是又怎么样?那混蛋想独吞鸦片,
还敢打我姑妈的主意!我杀他的时候,他还求我留他一命,
说知道谁画的符...""谁画的符?"林瞎子追问。
"他说..."那人的声音突然低下去,像是被什么东西堵住了嘴,
"是...是城隍庙那个..."话没说完,后堂的窗户突然"哗啦"一声被撞开,
一股冷风卷着雨水灌进来。林瞎子听见张彪大喊"抓住他",还有桌椅倒地的声音。
等他摸到窗边时,只抓到一片衣角,带着熟悉的檀香味,跟城隍庙香炉里的味道一模一样。
"跑了!"张彪喘着粗气,"往城隍庙方向跑了!"林瞎子的指尖在那片衣角上摩挲着。
布料很粗糙,是庙里道士穿的那种道袍料子。他忽然想起师父留下的那本《阴符经》,
里面夹着张黄纸,上面画着跟死者额头一模一样的乾卦,旁边还写着一行小字:"乾为天,
杀无赦"。雨还在下,城隍庙的钟声又响了起来,这次却只敲了两下,像是在催促着什么。
林瞎子握紧竹杖,转身往门口走去。他知道,接下来要去的地方,才是所有事情的根源。
3 城隍庙的道士城隍庙的香灰味比绸缎庄浓十倍。林瞎子刚走到前殿,
就听见道士们诵经的声音,咿咿呀呀的,混着木鱼声,在雨幕里飘得很远。"这位施主,
"一个年轻道士拦住他,声音脆生生的,"今日不对外开放。
"林瞎子的竹杖在地上顿了顿:"我找你们住持。""住持正在闭关。
"年轻道士的声音里带着警惕,"施主请回吧。"林瞎子没动。他听见后殿传来咳嗽声,
很轻,却很熟悉,跟绸缎庄后堂那个男人的咳嗽声一模一样。他把竹杖往旁边一挪,
正戳在年轻道士的脚边,那道士"哎哟"一声跳开,发出慌乱的响动。"让他进来。
"一个苍老的声音从后殿传来,带着浓重的鼻音,像是患了风寒。林瞎子摸索着往后殿走。
地上铺着青石板,缝隙里长满了青苔,踩上去滑溜溜的。他听见诵经声停了,
还有人悄悄跟在后面,脚步声很轻,像是怕被发现。后殿里摆着尊泥塑的城隍像,
身上的金漆掉了大半,露出里面的黄土。一个穿着道袍的老道士正坐在蒲团上,
手里捻着佛珠,念珠的碰撞声很规律,像是在计算着什么。"林先生大驾光临,
"老道士的声音里带着笑意,"不知有何贵干?"林瞎子在他对面的蒲团上坐下,
竹杖斜斜靠在腿边,铁皮底端与青石板相触,发出细微的共鸣。“住持认得我?
”老道士轻笑一声,念珠停在指间:“这县城里,谁不认得‘乾坤堂’的林瞎子?
去年王掌柜的事,先生可是帮了官府大忙。
”林瞎子指尖在膝头轻轻敲着:“王掌柜额头上的符,住持见过吗?
”念珠的碰撞声突然断了。过了片刻,老道士才缓缓开口:“道家符箓,种类繁多,
贫道眼拙,没见过那种样式。”“可有人说,”林瞎子的声音压得很低,像雨丝钻进泥土,
“那符是城隍庙画的。”后殿的空气仿佛凝固了。林瞎子听见老道士的呼吸变得粗重,
还有殿外年轻道士慌乱的脚步声,像是在往这边跑。他忽然侧过脸,
对着左侧的立柱说:“躲在柱子后面的那位,不用藏了。你的咳嗽声,在绸缎庄我就听过。
”立柱后传来一阵响动,王掌柜的侄子跌跌撞撞地走出来,右手上的布条已经被血浸透,
脸色白得像纸。“你...你别胡说!”他指着林瞎子,手却抖得厉害,“我没躲!
”老道士突然站起身,道袍的下摆扫过蒲团,发出沙沙的响。“明尘,不得无礼。
”他转向林瞎子,语气里带了几分冷意,“先生今日来,到底想查什么?”“查符。
”林瞎子的指尖摸到竹杖顶端的铜箍,那是他师父特意找人打的,据说能镇邪,
“赵大奎死前,说知道画符的人是谁。他提到了城隍庙,还没说完就被人打断了。
”王掌柜的侄子突然往老道士身后缩了缩,像是想把自己藏起来。
林瞎子听见他牙齿打颤的声音,比在黑风口时更急,像是怕极了眼前的老道士。
“先生是怀疑贫道?”老道士的声音陡然拔高,殿里的烛火猛地跳了跳,“贫道潜心修道,
从不杀生,怎会画那种邪符?”“可这符,”林瞎子从怀里掏出赵大奎夹层里的半张黄纸,
“用的是城隍庙特有的朱砂。这种朱砂掺了松香,画出来的符会发暗,
只有你们后山的丹房能配出来。”老道士的呼吸顿了顿。
林瞎子听见他往丹房的方向瞥了一眼,那里的门紧闭着,门缝里透出淡淡的红光,
像是在烧什么东西。“丹房里在烧什么?”林瞎子问。“没...没什么。
”年轻道士突然插嘴,声音发紧,“是...是烧旧符纸,每年都要烧的。”林瞎子站起身,
竹杖往丹房的方向探了探:“我能去看看吗?”“不行!”老道士厉声喝道,“丹房是禁地,
岂能让外人随便进?”就在这时,丹房里突然传来“砰”的一声,像是有什么重物倒了。
紧接着,一股焦糊味飘了出来,混着朱砂的气息,闻着格外刺鼻。张彪立刻拔出手枪,
子弹上膛的声音在安静的后殿里格外清晰:“里面有人!”老道士的脸色瞬间变了,
转身就想往丹房跑,却被张彪一把抓住。“让开!”张彪的力气极大,
把老道士按在城隍像上,发出“咚”的闷响。林瞎子摸索着推开丹房的门。门轴锈得厉害,
发出刺耳的吱呀声。屋里的焦糊味更浓了,他的竹杖往前探了探,触到一个软软的东西,
像是人的手臂。“点灯。”林瞎子说。张彪划了根火柴,火光亮起的瞬间,
所有人都倒吸一口凉气。丹房的角落里,一个穿着道袍的中年道士趴在地上,
后背插着把匕首,鲜血浸透了道袍,在地上积成一滩。而他面前的火堆里,
还在燃烧着些黄纸,纸上的朱砂符在火光中扭曲,
正是跟王掌柜、赵大奎额头上一模一样的乾卦。“是...是玄清师兄!
”年轻道士失声叫道,“他负责看管丹房的!”林瞎子蹲下身,指尖摸到中年道士的手腕,
已经凉透了。他顺着手臂往上摸,摸到道士的脸颊,眼角有泪痕,像是死前哭过。
再往旁边摸,摸到个烧焦的纸团,展开一看,上面用毛笔写着几个字:“十年前的债,
该还了”。“十年前?”张彪皱起眉头,“十年前发生过什么?”老道士突然瘫坐在地上,
喃喃自语:“报应...都是报应...”林瞎子转向他:“十年前,到底发生了什么?
”老道士的声音抖得不成样子:“十年前...这里不是城隍庙,
是个义庄...义庄里烧死了七个人,
都是...都是被冤枉的小偷...”林瞎子的指尖猛地一颤。他想起师父临死前说的话,
师父就是十年前从义庄跑出来的,当时半边脸都被烧伤了,手里还攥着半张黄纸符。
“那些人,”林瞎子的声音发紧,“是被谁烧死的?
”“是...是王掌柜和赵大奎的爹...”老道士的声音里带着哭腔,“他们当时是粮商,
说义庄里的人偷了他们的粮食,
就...就放了把火...”王掌柜的侄子突然尖叫起来:“不是我爹!
是他们自己不小心失火!我爹是被冤枉的!”“冤枉?”林瞎子冷笑一声,
从怀里掏出师父留下的那半张符,“这符上的笔迹,跟玄清道士的一模一样。十年前,
是他给那些冤死的人画的往生符吧?”老道士点了点头,
泪水混着鼻涕往下流:“玄清当时是义庄的看守,他劝不住那些粮商...只能给死者画符,
求他们安息...可谁知道,十年后,
王掌柜和赵大奎会接连出事...”林瞎子的竹杖在焦黑的地面上画着圈。十年前的火,
十年后的符,王掌柜卖绸缎换鸦片,赵大奎劫货要挟,
玄清道士被灭口...所有的线索像乱麻,却隐隐指向一个人。
“玄清为什么要杀王掌柜和赵大奎?”张彪问。“不是他杀的。”林瞎子站起身,
竹杖指向王掌柜的侄子,“是你杀了赵大奎,又杀了玄清,想嫁祸给城隍庙,对不对?
”那侄子脸色一白,连连后退:“不是我!我没有!”“你姑丈知道你爹当年放火的事,
一直良心不安,才沾了鸦片想麻痹自己。”林瞎子的声音越来越冷,
“赵大奎拿这事要挟你姑丈,你怕事情败露,就杀了他。玄清道士知道真相,
你又杀了他灭口,还故意在丹房放火,想烧掉证据。”“证据呢?”侄子梗着脖子喊道。
林瞎子的指尖摸到玄清道士的口袋,掏出一个玉佩,上面刻着个“王”字。
“这是你姑丈给玄清的吧?十年前,你爹放火后,给了玄清一笔钱封口,这玉佩就是信物。
你杀玄清的时候,他攥着玉佩,想留下线索。”侄子的腿一软,瘫在地上,再也说不出话。
张彪上前铐住他,铁铐碰撞的声音在丹房里格外刺耳。雨还在下,城隍庙的钟声又响了,
这次敲了七下,像是在告慰十年前的冤魂。林瞎子走出丹房,站在雨中,任凭雨水打在脸上。
他想起师父说过,算命算的不是命,是因果。十年前的因,结了十年后的果,谁也逃不掉。
“先生,”张彪走过来,把银镯子递给林瞎子,“这镯子怎么办?
”林瞎子摸了摸镯子上的缺口,突然想起李老四说过,这是赵大奎娘给的,保命用的。
可命数终究敌不过因果,再灵的镯子也护不住作恶的人。“扔了吧。”林瞎子说,
“让它陪着那些冤死的人。”张彪点点头,把镯子扔进了后殿的古井。扑通一声,
井水溅起涟漪,像是把所有的恩怨都沉进了水底。林瞎子转身往庙外走,竹杖敲在青石板上,
笃笃的响,像是在跟过去告别。他知道,这县城里的事还没完,因果循环,
总有新的故事在等着他。雨渐渐小了,阳光从云层里钻出来,照在城隍庙的金顶上,
反射出刺眼的光。林瞎子的影子被拉得很长,在湿漉漉的地上,像一道解不开的卦。
4 古井里的秘密张彪押着王掌柜的侄子离开后,城隍庙渐渐安静下来。
年轻道士在收拾丹房的残局,老道士则跪在城隍像前,不停地诵经,声音里还带着哭腔。
林瞎子站在前殿的廊下,听着雨滴从屋檐滴落的声音,一下一下,像是敲在人心上。“先生,
”一个怯生生的声音响起,是那个年轻道士,他端着碗热茶走过来,“喝点暖暖身子吧。
”林瞎子接过茶碗,指尖触到温热的瓷壁,心里却没什么暖意。“玄清道士,”他缓缓开口,
“十年前,他是不是还救过一个人?”年轻道士愣了愣,挠了挠头:“师父说过,
十年前那场火,确实有人从义庄跑出来,半边脸都烧伤了,是玄清师兄把他藏在丹房,
给了他些盘缠,让他远走高飞...难道先生认识那人?”林瞎子的指尖在茶碗边缘摩挲着。
师父当年就是这样离开的,他总说欠玄清一条命,却没想到,
十年后玄清会以这样的方式离开。“他藏没藏什么东西在庙里?”林瞎子问。
年轻道士想了想:“好像...玄清师兄总往那口古井旁边去,有时候能待上大半天。
前几天我还看见他往井里扔了个木盒子,不知道是什么。”林瞎子站起身,
竹杖往古井的方向探了探。那口井在后殿的角落里,井沿长满了青苔,
上面盖着块厚重的石板,看起来有些年头了。他走到井边,指尖摸到石板上的凹槽,
像是被人反复撬动过。“能帮我把石板挪开吗?”林瞎子问。年轻道士费了九牛二虎之力,
才把石板推开一条缝。一股潮湿的霉味从井里飘出来,混着淡淡的铁锈味。
林瞎子的竹杖往下探了探,大约丈许深的地方,触到个硬邦邦的东西,像是木盒的边角。
“有东西。”林瞎子说。年轻道士找来根绳子,系在竹杖上,慢慢往下放。
绳子放了约莫三丈,突然一沉,像是勾住了什么。两人合力往上拉,拉出一个巴掌大的木盒,
盒子上了锁,锁眼已经锈死了。林瞎子摸索着把盒子揣进怀里:“这盒子我先带走,
若是有什么线索,再告诉你们。”年轻道士点点头,看着林瞎子的背影消失在庙门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