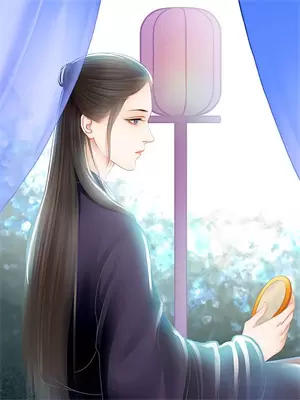第一章 阴风断杠李二庆讨厌这种湿冷。灰蒙蒙的天空压得很低,沉甸甸的,
好像随时都会塌下来。空气里混着泥土的腥气和纸钱烧过的焦味。他脚上的皮鞋沾满了泥,
裤腿也湿了,冰冷的湿气顺着布料往皮肤里钻。队伍走得很慢,安静得让人心慌。
前面是八个抬棺材的壮汉,簇拥着一口黑漆漆的木棺。老村长李满囤就躺在里面。
李二庆跟在人群中间,是李家旁支的亲戚,按辈分得叫李满囤一声“二爷”。
他身上套着一件不合身的白色孝服,廉价的布料磨的脖子有些发痒。他三天前从城里赶回来,
一下长途车,那股熟悉的乡土气息就扑面而来,让他总想逃离。他已经五年没回过李家村了。
队伍前方,老村长的长子李福贵正领着路,他腰板挺的笔直,脸上没什么表情,
只是偶尔回头,用眼神催促后面的人跟上。村里上了年纪的老人跟在棺材两侧,一边走,
一边往天上撒纸钱。白色的纸片在阴风里打着旋,有的飘出去很远,
有的却像是被什么东西拽住了,直直的落回棺材盖上。李二庆的目光落在棺材上。
那口棺材是村里最好的木匠打的,用了最好的松木,漆黑的棺身在昏暗天色下泛着一层油光。
他皱了皱眉,掏出手机看了一眼。没有信号。他把手机塞回口袋,抬头时,队伍停了。
前面传来一阵骚动。“怎么回事?”“歇歇脚吧,这坡不好走。”李二庆踮起脚朝前看。
送葬的队伍正走到村后的一处土坡上,这是去祖坟必须经过的路。坡不陡,但路面湿滑,
全是烂泥。“都加把劲,快到了!”李福贵的声音传来,带着不容置疑的口气。
八个抬棺的汉子应了一声,重新调整肩膀,把沉重的棺材扛稳。他们脸憋的通红,
额头上全是汗珠。就在他们迈出第一步时,一阵邪风毫无征兆的从坡上刮了下来。风不大,
却冷的刺骨。它卷起地上的落叶和纸钱,打在人们脸上,发出“沙沙”的响。
队伍里有人忍不住打了个哆嗦。李二庆也感到脖子后面一凉。“咔嚓!”一声脆响。
声音不大,但在死寂的队伍里却格外清楚。所有人都停下了脚步。李二庆看见,
走在棺材左前方的那个汉子,脚下的扁担发出了一声呻吟,一寸寸的弯了下去。
那根手臂粗的硬木杠子,中间裂开了一道口子。抬棺的几个人脸色瞬间变了。“稳住!
都稳住!”李福贵大吼一声,第一个冲了过去。晚了。断裂声接踵而至。木屑飞溅,
左前方的杠子彻底断成了两截。巨大的棺材猛的朝一侧倾斜,
另外七个汉子根本扛不住这股力道,纷纷脱手。“轰隆”一声闷响,
黑色的棺材重重砸在泥地里,一头陷进了烂泥中。人群发出一片惊呼。
几个老人吓的脸都白了,嘴里哆哆嗦嗦的念叨着什么。“都闭嘴!”李福贵脸色铁青,
冲着人群吼道,“就是木头旧了,有什么好大惊小怪的!”他一边骂,一边招呼人手,“快,
都过来帮忙,把棺材抬起来!”李二庆没有动。他的视线死死的盯着那口棺材。
刚才棺材落地的一瞬间,他清楚的看见,那严丝合缝的棺材盖,似乎震开了一条细缝。
一股难以形容的气味从那缝隙里飘了出来,像是陈年烂木头混合着什么东西腐败的味道。
风也恰好在这时停了。折腾了快半个小时,棺材才被重新抬上新的杠子。李福贵骂骂咧咧,
又找了几个年轻力壮的补了上去。下葬的过程很顺利,没有再出什么幺蛾子。
李二庆站在人群的最后面,看着村民们一铲一铲的往坑里填土,
直到那口黑色的棺材被黄土彻底掩盖。他胃里像是打了结,一股说不出的感觉越来越重。
他想起了爷爷。爷爷是村里最后一个道士,李二庆从小跟着他学过一些皮毛。画符,念咒,
看风水。爷爷总说,他们这一脉,欠着村子的债,要一代代还下去。李二庆不信这个。
他觉得那是迷信,是束缚。所以他考上大学,拼了命的也要留在城里。爷爷去世的时候,
他都没回来。现在,站在这片埋着祖辈的土地上,他第一次对自己坚信的科学,
有了一丝动摇。刚才那阵风,那根断掉的杠子,还有那股味道……他甩了甩头,
想把这些想法赶出脑子。巧合,都是巧合。葬礼结束,人群渐渐散去。李福贵走到新坟前,
点了三炷香,又烧了一沓纸钱。“爹,您老安心上路吧。”他低声说了一句,便转身离开,
招呼着亲近的几户人家去他家吃席。李二庆没有去。他找了个借口,
独自回了爷爷留下的老屋。***夜深了。李家村陷入一片黑暗,
只有零星几户人家还亮着灯。李二庆一个人坐在老屋的院子里,就着一盘花生米,喝着闷酒。
桌上那瓶从城里带回来的二锅头,已经空了一半。
酒精反倒让白天那些诡异的画面在脑子里愈发清晰。他想不通。李满囤在村里德高望重,
当了几十年村长,谁家有困难他都帮。这样一个人,怎么会连下葬都不安生?
村里的狗开始叫了。起先是东头的一只,叫声尖锐又急促。紧接着,
整个村子的狗都跟着狂吠起来。此起彼伏的狗叫声在寂静的夜里搅得人心烦意乱。
李二庆皱了皱眉,又灌了一口酒。乡村的夜晚就是这样,一点动静都能传出很远。
可今晚的狗叫声,似乎有些不一样。那声音尖利又恐慌,像是看到了什么可怕的东西。突然,
所有的声音都消失了。毫无征兆。前一秒还是震耳欲聋的狂吠,后一秒,
整个世界就陷入了死寂。连虫鸣声都听不见了。李二-庆握着酒杯的手停在半空。
一股寒意顺着他的脊椎爬了上来。他能听见自己的心跳声,一下,又一下,像是擂鼓。
院门外传来一阵急促的脚步声,接着是“砰砰砰”的砸门声。“二庆!二庆!快开门!
”是村民王老憨的声音,带着哭腔。李二庆放下酒杯,走过去拉开门栓。
王老憨连滚带爬的冲了进来,一屁股坐在地上,脸色惨白,浑身抖的像筛糠。
“鬼……有鬼啊!”他指着村东头的方向,牙齿都在打颤。“慢点说,怎么了?
”李二庆扶住他。“村长……村长坟头上……坐着个女人!”王老憨语无伦次,
“穿……穿着红嫁衣!”李二庆心里咯噔一下。“你看清楚了?”“看得清楚!我起夜撒尿,
就看见了!她就坐在那新坟上,背对着村子!”王老憨快哭了,“还有……还有那些纸人,
都活了!都在动!”李二庆的酒意瞬间醒了一大半。他骨子里那点唯物主义的想法还在挣扎。
或许是王老憨眼花了,或许是有人在恶作剧。“你在这待着,我去看看。”他说。
“别去啊二庆!会没命的!”王老憨死死的拽住他的裤腿。李二庆挣开他,
从墙角抄起一把柴刀。刀刃已经有些锈了,但握在手里,总算多了点底气。他深吸一口气,
拉开院门,走了出去。村里的小路没有灯,全靠天上的那点月光。今晚的月亮很暗,
被厚厚的云层遮着,只能透出一点模糊的轮廓。四周静的吓人。他握紧柴刀,
凭着记忆朝村后的坟地走去。越靠近,空气就越冷。他远远的停下脚步,
躲在一棵老槐树后面。他看见了。新堆起的坟包上,真的坐着一个身影。那是一个女人,
穿着一身鲜红的嫁衣。嫁衣的款式很老旧,在夜色中红的刺眼。她就那么静静的坐着,
乌黑的长发垂下来,遮住了脸。坟前,白天烧的那些纸人纸马,歪歪扭扭的站着。
其中一个纸扎的仆人,正对着坟头,一拜,一起,动作僵硬又诡异。
李二庆感觉全身的血液都凉了。这不是幻觉。就在他准备悄悄的退走时,
更可怕的事情发生了。那个纸人停下了动作。它缓缓的,缓缓的转过头,
那张用笔墨画出来的五官,正对着李二庆藏身的方向。纸人咧开嘴,露出一个僵硬的微笑。
一个干涩扁平,不似人声的声音,从那张纸糊的嘴里传了出来。“爹,
井里的娘问您啥时候下来。”声音不大,却像一把冰锥,狠狠的扎进了李二-庆的耳朵里。
爹?井里的娘?他脑子里一片空白,唯一的念头就是跑。他转过身,用尽了平生最大的力气,
疯了一样的往家的方向冲去。他不敢回头,他能感觉到,那道冰冷的视线一直粘在他的背上。
风声在耳边呼啸,脚下的路变得无比漫长。“砰!”他一头撞开自家的院门,反手插上门栓,
背靠着冰冷的门板,大口大口的喘着气。王老憨还瘫在院子里,看见他这副样子,
吓的更是说不出话。李二庆没有理他,他冲进里屋,在爷爷的遗物里疯狂的翻找起来。
他记得,爷爷有个从不离身的木箱子,上了锁,谁也不让碰。他找到了。箱子就塞在床底下,
上面积了一层厚厚的灰。锁是老式的铜锁,李二庆顾不上找钥匙,直接用柴刀把锁头砸开。
箱子打开,里面只有一本用牛皮纸包着的老旧线装书。书的封面上,
用毛笔写着三个字:道术手札。李二庆颤抖着手,翻开了书页。***天亮了。
阳光驱散了黑暗,却没能驱散笼罩在李家村上空的恐惧。李二庆一夜没睡。
他把老屋的门窗都关的死死的,就着一盏昏暗的油灯,看了一整夜的手札。
手札上的字都是用毛笔写的繁体字,内容晦涩难懂,
大多是画符的法门、念咒的口诀和一些阴阳五行的理论。他看的头昏脑胀,
却找不到任何关于红衣女人和纸人开口的信息。天一亮,他就听见了外面的哭喊声。
他打开一条门缝朝外看。村里彻底乱了。家家户户的门窗上,都出现了一个个血红色的手印。
那手印很小,像是个女人的手,颜色鲜红,好像刚从血里捞出来印上去的。更诡异的是,
手印是从门板和窗户的木头里渗出来的,像是木头自己在流血。村民们聚在村里的空地上,
人人脸上都带着慌乱。“这是怎么回事啊!遭了什么瘟了!”“我家的狗昨晚就不叫了,
今天早上起来一看,躲在窝里直发抖,喂东西也不吃!”“我家的也是!”李二庆走出去,
来到自家门前。他家的门上也有,一个鲜红的手印,印在门板正中央。他伸出手,
小心翼翼的碰了一下。那手印摸上去是干的,却带着一股冰冷的、黏腻的触感。
还有一股淡淡的腥味。李福贵从人群里挤了出来,他脸色也很难看,但还在强作镇定。
“都慌什么!是哪个搞的恶作剧!”他大声喊道,“找点水洗了就是!
”一个村民立刻提了桶水,用抹布使劲去擦门上的手印。可那手印就像是长在了木头里,
越擦,颜色反而越红,还隐隐有血丝从木纹里渗出来。那个村民吓的扔掉抹布,
一屁股坐在地上。人群彻底炸开了锅,恐慌迅速蔓延。李福贵也愣住了,
他看着自家门上那几个格外鲜红的手印,嘴唇动了动,一个字也说不出来。
李二庆没有再看下去。他退回院子,关上门,把门栓死死的插上。他知道,这不是恶作剧。
那个女人……那个怨魂,回来了。他回到屋里,拿起那本《道术手札》,深吸一口气,
从第一页开始,一个字一个字的重新看了起来。他必须找到答案。手札的纸张已经泛黄发脆,
墨迹也有些淡了。他一页一页的翻过,那些曾经被他视为封建糟粕的符文和口诀,
此刻却成了他唯一的希望。他看到了一段关于“镇物”的记载。“阳宅有煞,
可立镇物以安之。石敢当、八卦镜,皆可为用。然大凶之物,需以大煞镇之,血亲之骨,
法器之灵,方可压其百年。”他又看到了关于“怨”的描述。“含冤而死,怨气不散,
聚而成形。尤以血衣者为甚,此为血煞,索命讨债,不死不休。
”索命讨债……李二庆的心猛的一沉。他疯狂的往后翻,书页在他指尖哗哗作响。他总觉得,
爷爷一定留下了什么关键的线索。终于,他翻到了手札的最后一页。这一页是空白的。
李二庆愣住了。怎么会是空白的?他不信邪,把书页对着光亮仔细看,
又用手在上面反复摩挲。纸张很粗糙,没有任何夹层或者暗记。线索就这么断了?
就在他准备把书合上时,指尖无意中沾到了一点油灯里渗出的灯油。
他下意识的在最后一页的空白处蹭了一下。被灯油浸过的纸面上,
缓缓的浮现出了一行行暗红色的小字。那颜色,像极了干涸的血迹。字迹潦草,
笔画仓促又颤抖,看得出写字的人当时很恐惧。李二庆的心跳到了嗓子眼,他凑近油灯,
辨认着那些字。“一九六二,大旱,无粮。”“邪道过村,言可以人换粮,七命换七百斤。
李满囤……应允。”“以祭天为名,骗杀七人于古井。赵氏巧云,新婚三日,着嫁衣,
首当其冲。”“我阻之,未果,反受其胁……愧对祖师。”“此乃血债,李氏一族,
世代难偿。怨魂索命,必从头七始……”看到这里,
李二庆手里的手札“啪”的一声掉在了地上。他全身的力气仿佛都被抽空了。原来,
德高望重的二爷,受人敬仰的老村长,手上竟然沾着七条人命。原来,这不是普通的闹鬼。
这是六十年前的怨魂,回来讨债了。第二章 血债索命李二庆的后背抵着冰冷的墙,
手札上的字迹像是一条条扭动的血虫,钻进他的眼睛,爬满他的大脑。一九六二。人换粮。
七条人命。赵巧云。古井。这些词汇串联在一起,勾勒出一桩被黄土掩埋了六十年的罪恶。
爷爷的愧疚,李满囤的伪善,还有昨晚纸人那句“井里的娘”,
所有碎片都在这一刻拼凑完整。头七。怨魂索命,必从头七始。今天,
是李满囤下葬的第二天。李二庆的呼吸变得急促。恐惧不再是模糊的感觉,
而是变成了具体的时间和目标。七天,他只有七天时间。他冲出里屋,
院子里的阳光有些刺眼。王老憨早就跑了,院门大开着,
门板上那个血手印在阳光下显得不那么狰狞,却依旧刺目。不能坐以待毙。
他想起了手札里那些画符的法门。爷爷教过他最基础的几种,但他从来没当回事,
只当是童年的游戏。现在,这是他唯一能抓住的稻草。他回到屋里,翻箱倒柜。
爷爷的东西不多,但都很齐整。他找到了一个木盒,里面装着一沓裁剪好的黄纸,一块朱砂,
还有几支狼毫笔。李二庆深吸一口气,努力回忆着爷爷当年的样子。他研开朱砂,铺好黄纸,
提起笔。手有些抖。他画的是最简单的“安宅符”。一气呵成,中途不能断。第一张,
笔尖一顿,朱砂在纸上晕开一个墨点。失败了。他扔掉废纸,重新开始。第二张,画到一半,
脑子里闪过红衣女人的背影,手一抖,符文走了形。又失败了。他额头渗出细汗,
强迫自己冷静下来。他闭上眼,脑中观想着符文的每一个转折。第三次,他终于一笔画完。
符文歪歪扭扭,远没有爷爷画的那么有气势,但总算是成了。他长出了一口气,
感觉像是跑了几里山路一样疲惫。他把这张符贴在了自家大门上,正对着那个血手印。
他又画了几张,一张给了隔壁吓破了胆的王老憨,一张塞进了自己怀里。做完这一切,
他看着李福贵家的方向,犹豫了一下。李福贵是李满囤的儿子,是血债的第一顺位继承人。
他家门上的血手印,比任何一家都多,都红。他最终还是没有去。他现在去找李福贵说这些,
只会被当成疯子打出来。***夜色再次降临。李家村的夜晚,从来没有这么安静过。
没有狗叫,没有人声,家家户户门窗紧闭,像是躲避瘟疫。李二庆坐在院子里,
手里握着那把生锈的柴刀。他没有点灯,只是借着微弱的月光,
死死盯着大门上那张黄色的符纸。子时刚过,风起了。不是白天的阴风,
而是一股带着水汽的、腥冷的风。风吹过院子,卷起地上的几片落叶。门外,传来了滴水声。
“滴答……滴答……”声音很轻,很有规律,像是屋檐漏水。但今晚并没有下雨。
李二庆站起身,一步步挪到门后,透过门缝往外看。他什么也没看见。外面空无一人。
但那滴水声却越来越近,最后就停在他家门口。“滴答……”一滴暗红色的液体,
从门板上那个血手印的指尖渗了出来,滴落在门前的石阶上。紧接着,是第二滴,第三滴。
那个手印,像是活了过来,在流血。门上的那张安宅符,没有任何反应。
李二庆的心沉到了谷底。他听见屋里传来“噗通”一声。他猛地回头,冲进里屋。屋子正中,
摆着一口储水的大水缸。缸口用一块木板盖着。刚才的声音,就是从水缸里传出来的。
他死死盯着那口水缸,握着柴刀的手因为用力而指节发白。水缸里很安静。或许是听错了?
他慢慢走过去,伸出手,搭在了盖板的边缘。木板很重,他用了些力气才将它掀开。
水面很平静,倒映着窗外惨淡的月光。水缸里什么都没有。李二庆松了口气,
觉得自己有些神经过敏。就在他准备把盖板重新盖上时,他看见水面上,
缓缓浮起了一根黑色的东西。很长,很细。是一根头发。紧接着,第二根,
第三根……一团乌黑的、湿漉漉的头发,从水底冒了上来,像一团水草,在水面慢慢散开。
一股浓烈的腥臭味,从水缸里弥漫开来。李二庆胃里一阵翻江倒海,他连连后退,
后背重重撞在墙上。他想起了爷爷手札里的记载。“怨魂索命,五行皆可为凭。遇水化形,
遇木留痕……”这东西,已经进到他家里来了。他画的符,根本没用。***天亮后,
李二庆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把那口水缸砸了。他几乎一夜没睡,坐在院子里,
直到第一缕阳光照进来。简单的道法没用,说明这怨魂的怨气远超想象。
他需要知道更多六十年前的细节。手札上提到了七个死者,但只点了赵巧云的名字。
剩下六个人是谁?当年除了李满囤,还有谁参与了这件事?这些问题的答案,
只有还活着的老人知道。他锁上院门,径直朝着村西头走去。村西头住着李四爷,
是和李满囤同辈的人,八十多岁了,腿脚不便,很少出门。李二庆小时候,还叫过他四爷爷。
李四爷家门窗紧闭,门上的血手印像是被人用刀刮过,留下一道道凌乱的划痕,
血色反而更深了。李二庆敲了敲门。里面没有动静。“四爷爷,是我,二庆。”他提高声音。
过了好一会儿,门才开了一道缝。李四爷苍老的脸出现在门后,布满了警惕和恐惧。
“你来干什么?”他的声音沙哑干涩。“四爷爷,我想问点事。”“没什么好问的,
村里遭了邪,你赶紧回城里去吧,这儿不干净。”李四爷说着就要关门。
李二庆一把抵住门板。“四爷爷,我知道六十年前的事。”他压低声音,一字一句地说,
“人换粮。”李四爷浑身一震,浑浊的眼睛里瞬间充满了惊恐。他像是被踩了尾巴的猫,
尖叫起来:“你胡说什么!没有的事!你快走!”他用力推门,
但李二庆的手像铁钳一样纹丝不动。“赵巧云,新婚三天,穿着嫁衣被推进了古井。
”李二庆继续说,每一个字都像钉子一样敲进老人的心里,“还有另外六个人。您当年,
应该在场吧?”“我不在!我什么都不知道!”李四爷的脸涨成了猪肝色,他挥舞着手臂,
想把李二庆推开。李二庆没有理会他的挣扎,目光扫过他昏暗的屋子。屋角,堆着一些杂物。
最下面,压着一个用麻绳捆着的旧麻袋。麻袋的样式很老,
上面还印着褪色的红色五角星和“丰收”两个字。那是那个年代特有的东西。
李二-庆的目光回到李四爷脸上,声音变得冰冷:“那七百斤粮食,您家也分了吧?
”这句话像是一把尖刀,彻底刺穿了李四爷的心理防线。他停止了挣扎,
全身的力气像是被抽空了,靠在门框上,嘴唇哆嗦着,却一个字也说不出来。
“我……我只是……帮忙抬了石头……”他终于从牙缝里挤出几个字,“他们说……填了井,
就没事了……”“井在哪?”李二-庆追问。
“就在……就在村东头那片荒地……”李四爷的声音带着哭腔,
“早就被填平了……上面都长了树了……”他说完,猛地把李二庆推开,
用尽全身力气“砰”的一声关上了门,里面传来落锁的声音。李二庆站在门口,没有再敲。
他已经得到了他想要的信息。***当天夜里,李四爷死了。
尸体是第二天早上被他儿子发现的。李二庆赶到的时候,李四爷家门口已经围满了人。
村民们的脸上,不再只是恐慌,还多了一丝麻木和绝望。李福贵也在,他黑着脸,
不让任何人靠近。李二庆挤进人群,看到了屋里的景象。李四爷就倒在堂屋中央,
眼睛瞪得老大,嘴巴也张得很大,像是要呼喊什么。他的嘴里,塞满了泥土和石子。
和手札里的描述一模一样。帮忙抬石头的人,最终死于石头。
人群中响起一片倒吸冷气的声音。ax“报应……这是报应来了……”一个老人喃喃自语。
“都给我闭嘴!”李福贵猛地回头,冲着人群怒吼,“谁再敢胡说八道,给我滚出李家村!
”他的咆哮没能吓住众人,反而让那股压抑的恐惧更加浓烈。村民们看着李福贵的眼神变了。
如果说之前只是怀疑,现在,很多人已经开始相信,这一切都和老村长李满囤脱不了干系。
而李福贵,作为他的儿子,自然也成了众人目光的焦点。“二庆!
”李福贵看见了人群中的李二庆,他大步走过来,一把抓住他的衣领,“是不是你!
是不是你昨天来找过他!你跟他说了什么!”“我只是问了些该问的事。
”李二庆挣开他的手,冷冷地看着他。“你……”李福贵气得发抖,指着李二庆,
却说不出话来。他知道,现在村里人心惶惶,如果他动了李二庆,只会让事情更糟。
“李福贵,”李二庆直视着他的眼睛,“你爹的债,现在要你们来还了。下一个是谁,是你,
还是你儿子?”李福贵的脸色瞬间变得惨白。李二庆没有再理他,转身离开了人群。
他心里没有一丝复仇的快感,只有沉甸甸的压抑。死了一个了。还剩下六个。不,
算上李满囤,是七个。那个怨魂在按照某种规则杀人。她不会停下,直到所有债都讨还干净。
他必须找到那口古井。那是怨气的源头,也是所有死者的归宿。李四爷说了,
古井在村东头的荒地。那片地方很大,要把一口被填埋了六十年的井找出来,
无异于大海捞针。他回到爷爷的老屋,再次翻开那本手札。他需要更直接的方法。
他在手札的后半部分,找到了一种名为“寻踪术”的法门。“以死者遗物为引,燃迷魂香,
可循其怨气所归之处。”死者的遗物……赵巧云已经死了六十年,哪还有什么遗物。
李二庆的目光落在了自家门板上那个血手印上。这东西是怨魂留下的,也算是遗物吧?
他找来一把小刀,小心翼翼地从血手印上刮下一些暗红色的木屑。他又按照手札上的记载,
用几种草药混合,制成了所谓的“迷魂香”。夜幕降临,他拿着东西,
独自一人走向村东头的荒地。今晚的月色很好,照得荒地一片清冷。这里曾经是耕地,
后来不知道为什么荒废了。地上长满了半人高的杂草,还有几棵歪脖子树。
李二庆找了个背风的地方,用石头垒了个简易的香炉。他将刮下的木屑放进香炉,
然后点燃了迷魂香。一股奇特的香味弥漫开来。他按照手札上的方法,盘腿坐下,
口中默念咒语,双眼紧紧盯着香炉里升起的烟。烟是青色的,起初笔直地向上飘,但很快,
就像是被什么东西牵引着,开始朝着一个方向缓缓移动。李二庆站起身,跟在烟后面。
青烟飘得很慢,在杂草丛中穿行,像一个沉默的引路人。李二庆的心提到了嗓子眼。
他不知道这烟会把他引向何方,也不知道路的尽头等着他的是什么。大约走了一炷香的功夫,
青烟在一片相对平坦的空地前停了下来。烟雾在这里盘旋,不再前进,最后慢慢散尽。
就是这里了。李二庆看着脚下的土地。这里寸草不生,和周围的杂草丛形成鲜明的对比。
地面是暗红色的,像是被血浸透过。他从背包里拿出带来的工兵铲,开始往下挖。泥土很硬,
挖起来很费力。挖了大概半米深,铲子碰到了一块硬物。-不是石头。是木头。
他清理掉周围的泥土,露出来的,是一块腐朽的圆形木板。是井盖。
第三章 安魂之阵李二庆的心脏在胸腔里剧烈跳动。他用工兵铲撬开腐朽的井盖边缘,
一股浓郁到化不开的阴冷气味混杂着泥土的腥味,从缝隙里喷涌而出。
这股气味比他之前闻到的任何一次都要刺鼻,像是无数尸体在狭小空间里腐烂了几个世纪。
他强忍着呕吐的欲望,用尽全身力气将那块沉重的木板掀到一旁。
一个漆黑的洞口出现在他面前。这就是那口吞噬了七条人命的古井。月光照不进井里,
只能看到一片深不见底的黑暗。李二庆打开带来的手电筒,一道光柱刺入其中。
井壁是青石砌成的,长满了滑腻的青苔。井不深,大概只有七八米的样子。井底没有水,
只有一层厚厚的、黑色的淤泥。淤泥之上,散落着一些白色的东西。是人骨。
李二庆的呼吸停滞了一瞬。他看到了一个完整的、蜷缩着的人类骨架,大部分都陷在淤泥里。
旁边还有几根散落的腿骨和肋骨。手电光继续往下移动。在井底的中央,
他看到了另一具相对完整的骸骨。那具骸骨保持着一个诡异的姿势,头骨深深地埋在淤泥里,
一只手臂的白骨高高举起,五根指骨张开,像是在向井口呼救,又像是在控诉着什么。
在那具骸骨的旁边,有什么东西在反光。不是骨头。李二庆调整手电的角度,
看清了那是什么。那是一块暗红色的布料,被淤泥包裹着,但依然能分辨出原本的颜色。
嫁衣的残片。赵巧云。李二庆关掉手电,坐在井边,沉默了很久。夜风吹过,
荒草发出沙沙的声响,像是在低声啜泣。他知道,自己必须下去。他从背包里拿出绳子,
一头绑在旁边一棵歪脖子树上,另一头扔进井里。他试了试绳子的牢固程度,
然后深吸一口气,顺着绳子滑了下去。井底的空气更加污浊,阴冷刺骨。脚下的淤泥很软,
一脚踩下去就没到了脚踝。他打开手电,光柱在狭小的空间里晃动。他看到了更多的骸骨,
有的被淤泥掩埋,只露出一部分,有的则被后来丢下来的石头砸得粉碎,和淤泥混在一起,
分不清彼此。他走到那具举着手臂的骸骨前,蹲了下来。这就是赵巧云。
他想把她的骸骨收敛起来,但骨头和淤泥已经半凝固在一起,稍一用力,
那脆弱的指骨就可能断裂。他的目光落在那只高举的手骨上。在张开的五根指骨中间,
似乎攥着什么东西。李二庆小心翼翼地拨开包裹着指骨的淤泥。
那是一个黑色的、巴掌大小的石牌。石牌的材质很奇怪,非石非木,入手冰冷。
上面刻着一些他看不懂的符号,像是某种符咒。这东西在手札里没有记载。
他刚想把石牌拿起来仔细看看,异变突生。石牌离开骸骨的一瞬间,
整个井底的温度骤然下降。一股无形的压力从四面八方挤压过来。
他耳边响起一声尖锐的、不似人声的哭嚎。那声音仿佛不是从某个方向传来,
而是直接在他脑子里炸开。手电筒的光闪烁了两下,熄灭了。
井底陷入一片伸手不见五指的黑暗。李二庆能感觉到,有什么东西,在黑暗中苏醒了。
淤泥里传来“咕嘟咕嘟”的声音,像是有什么东西要从下面钻出来。
他浑身的汗毛都竖了起来,想也不想就把那块石牌重新塞回了赵巧云的指骨中。
哭嚎声戛然而止。那股恐怖的压力也随之消失。他瘫坐在淤泥里,大口喘着气。
他重新打开手电,光亮驱散了黑暗,也照亮了他惨白的脸。刚才那一下,
他几乎以为自己要死在这里。他明白了。这个石牌,就是爷爷手札里提到的“镇物”。
是那个邪道留下来,用来镇压这七个怨魂的东西。李满囤的下葬,不是巧合。
他的坟就在这片荒地的正上方。新坟入土,活人阳气汇聚,冲撞了地下的阴气格局,
削弱了镇物的力量。怨魂因此得以脱困,但力量还不完整。所以她只是在坟头显形,
用血手印标记仇人。而自己刚才拿走镇物,等于彻底解开了最后的封印。
李二-庆看着手里的石牌,又看了看井底的骸骨。他知道,他不能再把这东西放回去了。
压制,只能换来一时的平静。六十年的怨气,一旦彻底爆发,整个李家村都将不复存在。
唯一的办法,是超度。他把石牌揣进怀里,对着井底的骸骨深深鞠了一躬。“各位,得罪了。
”他没有再动那些骸骨,而是转身抓住绳子,迅速爬出了古井。***这是第四天的夜里。
村子里的气氛已经压抑到了极点。李四爷的死像一块巨石,压在每个人的心头。白天的时候,
又有两户人家悄悄收拾东西,想开车逃走。但车子开到村口就熄了火,怎么也打不着。
他们被困住了。李二庆回到老屋,没有休息。他把爷爷的手札翻到最后几页,
那里记载着一个极其复杂的阵法。安魂阵。“集七七四十九人之阳火,取无根水、公鸡血,
辅以朱砂墨,立阵于怨气汇集之地。以血亲为引,诵安魂之咒,可化解百鬼之怨。
”这是手札里记载的、唯一能够超度血煞怨魂的法门。-但条件苛刻得近乎不可能。
七七四十九个青壮年男人,在这个人人自危的时候,谁肯出来?血亲为引……李满囤的血亲,
只有李福贵和他那个刚上小学的儿子。李二庆看着窗外李福贵家的方向,陷入了沉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