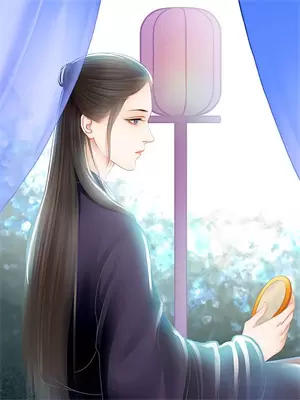京圈太子爷贺望被人下了降头,生命垂危,倒计时只剩七天。
贺家请遍了玄门高手都束手无策,最后找到了我这个在天桥底下贴膜的。
我慢悠悠地擦着手机膜,头也不抬:救他可以,让他入赘,给我家保家仙当三年长随。
贺望的母亲气得发抖,把一张黑卡摔在我面前:给你一千万,马上滚!我没动,
只是抬头看了眼她身后跟着的那个小鬼,幽幽道:夫人,您还是先关心关心自己吧。
你儿子只是快死了,而你,已经死了三天了。话音刚落,
她身后的小鬼冲我露出了一个诡异的微笑。1.我叫苏晚,在天桥下贴膜。下午三点,
一辆黑色的劳斯莱斯停在桥下,车上走下来一个珠光宝气的女人。她叫柳静姝,
京圈太子爷贺望的母亲。她身后的保镖清空了我的小摊周围,柳静姝居高临下地看着我,
眼里是毫不掩饰的鄙夷。你就是苏晚?我正给一部水果15Pro Max换钢化膜,
动作行云流水,没理她。她似乎习惯了被人捧着,我的无视让她很不悦。我儿子贺望,
想必你听过。他中了降头,只有七天可活。有人推荐了你,开个价吧。我终于贴好了膜,
用无尘布细细擦去表面的指纹,这才抬起头。救他可以,让他入赘,
给我家保家仙当三年长随。柳静姝的脸色瞬间铁青,保养得宜的脸上满是怒火。
你算个什么东西,也敢觊觎我儿子?她气得发抖,从爱马仕包里抽出一张黑卡,
狠狠摔在我面前的工具箱上。给你一千万,马上滚!金属卡片撞在塑料上,
发出沉闷的声响。我没动,目光越过她,看向她身后。那里站着一个穿着红肚兜的小鬼,
正抱着她的腿,冲我咯咯地笑。它浑身散发着尸体腐烂的恶臭,黑气几乎凝为实质。
我收回目光,看着柳静姝,语气平淡。夫人,您还是先关心关心自己吧。
你儿子只是快死了,而你,已经死了三天了。柳静姝像是听到了天大的笑话,
嗤笑一声:你咒我?我没回答。她身后的那个小鬼,却在这时松开了她的腿,
冲我露出了一个无比诡异的微笑,嘴巴咧到了耳根。2.大胆妖人,竟敢在此胡言乱语!
柳静姝身后的一个黑西装保镖厉声呵斥,伸手就要来抓我的领子。我没动,
只是静静地看着他。他的手在距离我一寸的地方停下,像是被一道无形的墙挡住了。
保镖脸色一变,再次发力,手腕却诡异地向后一折,发出咔嚓一声脆响。他惨叫着后退,
额头瞬间布满冷汗。柳静姝的脸色终于变了,她惊疑不定地看着我,
又下意识地摸了摸自己的身体。我……我怎么可能死了?我好端端地站在这里!是吗?
我轻笑一声,从工具箱里拿出一面小小的八卦镜,递到她面前,夫人不妨自己看看。
镜子里没有映出她雍容华贵的脸,只有一片灰蒙蒙的雾气。而在那雾气中央,
她身后那个红肚兜小鬼的脸,正清晰地浮现在镜面上,对着她笑。
柳静-姝的尖叫声刺破了天桥下的宁静。她踉跄后退,惊恐地指着镜子,
又指着我:你……你对我做了什么手脚!不是我对你做了什么,而是它对你做了什么。
我收回镜子,下巴朝那个小鬼的方向点了点。那个小鬼见被我点破,也不再伪装,
抱着柳静姝的腿,用一种不属于孩童的阴森声音撒娇:妈妈,我好饿啊,我要吃饭饭。
它一边说,一边张开嘴,狠狠咬在柳静姝的大腿上。没有鲜血,
只有一缕缕黑色的雾气从柳静姝的腿上被它吸进嘴里。那是她的魂体。
柳静姝发出一声更凄厉的惨叫,身体剧烈地颤抖起来,脸色以肉眼可见的速度变得灰败。
救我……快救我!她终于崩溃了,朝我伸出手,眼里的高傲荡然无存,
只剩下纯粹的恐惧。我依旧坐在我的小马扎上,不为所动。想让我救你,
可你刚刚不是让我滚吗?就在这时,另一辆黑色的宾利疾驰而来,一个穿着中山装,
面容威严的中年男人快步下车。贺望的父亲,贺正国。他身后跟着的助理正举着一个平板,
屏幕上赫然是我这里的实时监控。显然,他看到了刚才发生的一切。贺正国快步走到我面前,
没有丝毫犹豫,对着我深深一鞠躬。苏大师,方才是我夫人有眼不识泰山,
我代她向您赔罪。求您出手,救救她,也救救我儿子!3.贺正国的态度,
比柳静姝高明了不止一个档次。他很清楚,对于我们这种人来说,钱是最低级的收买方式。
尊重,才是唯一的通行证。我瞥了一眼被小鬼啃食得越来越虚弱的柳静姝,慢悠悠地站起身,
开始收拾我的贴膜工具。带路吧。贺正国大喜过望,连忙亲自为我拉开车门。上了车,
我才发现这辆宾利的后座被改造过,坐垫上刻着密密麻麻的符文,显然是出自某位高人之手,
用以隔绝阴气。可惜,没什么用。那个小鬼抱着柳静姝的魂体,轻而易举地就跟了上来,
还冲我做了个鬼脸。我懒得理它。贺家的老宅在西山,是一座戒备森严的中式庄园。
车子驶入庄园,我便感觉到一股浓郁的阴煞之气扑面而来,
其中还夹杂着南洋降头的诡异味道。客厅里,已经坐了七八个所谓的玄门高手。
一个个仙风道骨,捻着佛珠,或者手持拂尘,看见我一个穿着T恤牛仔裤,
拎着贴膜工具箱的小姑娘走进来,眼神都带上了几分轻蔑。正国,这就是你说的『高人』?
一个穿着八卦道袍的老者抚着山羊胡,语气不善,一个天桥底下贴膜的丫头片子,
你是不是急糊涂了?另一个脑满肠肥的和尚也宣了声佛号:贺施主,
令郎的状况非同小可,不可儿戏啊。贺正国脸色有些尴尬,但还是坚持道:各位大师,
苏大师是有真本事的。真本事?那道士冷笑一声,小丫头,
你可知贺少爷中的是什么降?可知此降如何解?我没理会这些跳梁小丑,径直穿过客厅,
走向二楼。贺正经想要跟上,却被那道士拦住:让她自己上去,我倒要看看,
她能看出什么门道来!若是装神弄鬼,耽误了贺少爷的救治,休怪我玄门不容!
我脚步未停。推开二楼卧室的门,一股混合着药味和腐臭的气息瞬间涌出。
价值千万的沉香木大床上,躺着一个面色青黑的年轻人。正是贺望。他双眼紧闭,嘴唇发紫,
胸口几乎没有起伏,手腕上缠着一串黑色的佛珠,但佛珠上的阳气已经耗尽,裂纹遍布。
床边的心电监护仪上,心跳曲线微弱得像一条垂死的蚯蚓。柳静姝的魂体飘在床边,一边哭,
一边徒劳地想去触摸儿子的脸。那个小鬼则蹲在床头,
贪婪地吸食着从贺望天灵盖冒出的最后一丝生气。我扫视一圈,
目光落在床头柜上一个精致的木雕娃娃上。娃娃的眉眼,和柳静姝有七分相似。
子母连心降。我淡淡开口,以母血为引,子命为祭,母死子随。下降头的人,
是想让你们贺家,断子绝孙。4.我的话音不高,却清晰地传到了楼下每一个人的耳朵里。
客厅里瞬间一片死寂。几秒后,那个山羊胡道士第一个发出嗤笑:一派胡言!
子母连心降早已失传百年,制作条件极为苛刻,岂是那么容易下的?小丫头,不懂不要装懂!
就是,我等在此研究了三天,都断定是普通的草人降,只是手法刁钻了些。
旁边的和尚附和道。贺正国的脸色却瞬间变得惨白。他快步冲上楼,
声音都在发抖:苏大师,您……您说什么?子母连心降?我没看他,
目光依然锁定在那个木雕娃娃上。下降头的人,取了柳夫人的心头血,混入你的血,
雕刻成这个木偶,埋在了贺家的地基之下。木偶是母,贺望是子。三日前,柳夫人车祸身亡,
母降被激活,子降随即发动,开始吞噬贺望的生机。我顿了顿,看向贺正国:那场车祸,
不是意外吧?贺正国的身体猛地一晃,几乎站立不稳。是……是一场意外,
肇事司机已经……肇事司机是不是当场死亡,并且死状凄惨,浑身血液都被抽干?
我打断他。贺正国瞳孔骤缩,骇然地看着我,一个字都说不出来。
柳静姝的魂体也停止了哭泣,呆呆地看着我,又看看自己的丈夫,似乎终于意识到了什么。
楼下的大师们也安静了。行家一出手,就知有没有。光凭看一眼,
就能说出降头的名称、原理,甚至点出柳静姝车祸的细节,这份眼力,他们拍马也赶不上。
山羊胡道士的脸一阵青一阵白,嘴唇哆嗦着,想反驳,却找不到任何话语。
那……那现在该怎么办?贺正国声音嘶哑,带着最后一丝希望,大师,求您救救犬子!
我终于收回了目光,看向他:我来的时候就说了条件。贺正国一愣,
随即毫不犹豫地用力点头:我答应!只要能救活小望,别说入赘给您的保家仙当长随,
就是要我贺家一半的家产,我也给!我对你家的钱不感兴趣。
我从工具箱里拿出一叠黄纸,一支朱砂笔,旁若无人地在房间中央的空地上画起了符阵。
想救你儿子,得先把你老婆送走。柳静姝的魂体猛地一颤,惊恐地看着我:送走?
去哪儿?我不要去投胎,我要陪着我儿子!她身边的那个小鬼也适时地发出尖锐的笑声,
用只有我能听到的声音说:想送走她?晚了,她已经是我的新妈妈了,谁也抢不走。
我笔尖一顿,抬头看了它一眼。是吗?一个不成气候的养路小鬼,也敢在我面前叫嚣?
小鬼的笑容僵在脸上。我没再理它,继续画符。繁复的金色符文在我笔下迅速成型,很快,
一个复杂的阵法就占据了房间的大半个地面。
我将最后三张符纸分别贴在贺望的额头、胸口和丹田,护住他的心脉。然后,
我从工具箱里拿出三根手臂粗的白蜡,立在阵眼。贺先生,我头也不抬地吩咐,
去准备一碗活公鸡的鸡冠血,一盆无根水,还有柳夫人出车祸时穿的衣服。
贺正国不敢怠慢,立刻转身去办。房间里只剩下我,昏迷的贺望,以及一鬼一魂。
柳静姝飘在我面前,神情戒备而哀求:苏大师,我求求你,不要伤害我儿子……闭嘴。
我冷冷打断她,你现在自身难保,还有空管别人?你以为你死了,就能安宁了?
我指着她脚下那个小鬼:它叫路阴童,是横死街头的婴孩怨气所化,
专在枉死之人的头七引路,代价是吸食其七成魂力。今天,是你的头七。柳静姝浑身剧震,
低头看向那个一直对她撒娇的小鬼,眼里满是不可置信。路阴童咧开嘴,
露出一口细密的尖牙,不再伪装。妈妈,时辰快到了,我们该上路了。
付费点它猛地张开嘴,一股强大的吸力从它口中传来,死死地拽住柳静姝的魂体。
柳静姝发出无声的尖叫,魂体被一点点拉扯变形,眼看就要被吸进小鬼的嘴里。聒噪。
我屈指一弹,一张符纸无火自燃,精准地贴在路阴童的脑门上。啊——!
路阴童发出一声凄厉的惨叫,抱着脑袋在地上打滚,
身上的黑气被符纸上的金光灼烧得滋滋作响。柳静姝压力一轻,瘫软在地,
魂体几乎变得透明。就在这时,异变陡生。原本躺在床上一动不动的贺望,
身体突然剧烈地抽搐起来,心电监护仪发出了刺耳的警报声,
那条微弱的曲线瞬间变成了一条直线!与此同时,房间里的阴气暴涨!
那个被我符纸镇压的路阴童,身上的黑气非但没有减弱,反而以一种恐怖的速度膨胀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