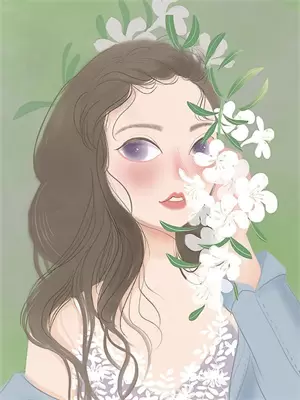
我左耳上的疤,是十年前那场大火留的。那天,我爸被压在拆迁房的水泥板下,
我攥着《自愿捐肾同意书》蹲在急救室外,纸边割得满手血。现在?更可笑了。
我天天帮开发商拆别人房子,自己的老家却要被我丈夫拆了。他亲我耳朵说情话时,
电视里推土机正轰隆隆铲我家的祠堂。第一章暴雨砸得伞面噼啪炸响,
伞柄突然硌进掌心——借着闪电惨白的光,“小耳朵”三个阴刻字像火钳烙进眼底。
那是我的耻辱烙印,十年前大火烧塌房梁时,邻居小孩对着我残缺的左耳叫嚷的绰号。
还记得那天......谢川猛地扳过我下巴,
嘴唇反复亲吻着那块扭曲的伤疤:“听不清怕啥?我当你一辈子耳朵。”一辈子的耳朵,
这是我听过最动听的话。在发现真相之前,对此我深信不疑。
以为我是这个世界上最幸运的人,幸运地遇到了他。黏湿的吐息声裹着谎言钻进我的耳道,
像蛞蝓在脑髓里爬行。让我大脑宕机。可没等我推开他,
身后电视“滋啦”爆出红光——“青石巷拆迁今早启动!
”主播的嗓音和推土机轰鸣绞成一团。屏幕里钢爪此刻正在撕碎我童年的秋千架,
槐木断裂声扎穿鼓膜,混着记忆深处父亲肋骨被压断的闷响。耳鸣轰然炸开,此刻,
雨声、钢履带碾轧声、火苗噼啪声在我的颅骨里沸腾着。左耳旧疤开始突突狂跳,
浓烟中父亲焦黑的手仿佛穿透岁月抓来:“闺女快跑——”记忆回到十年前。那天,
是我永远忘不掉的一天。谢川用他冰凉的指尖刮过我的后颈沟:“签了拆迁同意书,
你弟的肝源下周就能排上。”这句话像冰锥捅穿我的胸腔。让我浑身瞬间起了鸡皮疙瘩。
他转身时,突然,口袋里的病历本“啪”地滑落。纸边割裂雨帘的刹那,
视网膜:患者:林雨溪LYX肾源接收日:2022.4.2我感到全身血液瞬间冻结。
父亲死在2022年4月5日——原来他断气前三天,我的肾竟然被剜给这女人续命!
伞柄刻痕猛地活了过来,蜈蚣般顺静脉啃噬臂骨,推土机的钢齿在脑仁里疯狂刨掘。
左耳“嗡”地爆出火星,房梁倒塌的巨响与钢履带轰鸣重叠。
幻觉中父亲焦黑的手从火场伸出:“别信他们……”我失控地抠挠过敏泛红的掌心,
血珠滚在“LYX”字母上,油墨晕成父亲灼伤的脸庞:“你要把全家献祭光吗?
”染血的病历被谢川一把抽走:“明天拆祠堂,你妈的牌位还在供桌上。
”木槌砸中胸口般的钝痛中,雨幕扭曲成母亲遗照的凝视。
瓦片撕裂声混着父亲骨裂的记忆涌来,
左耳骤然坠入深海死寂——唯有弟弟的心跳监测仪嘀嗒声刺破虚空,
像推土机的钢爪在刨我家族的坟茔。
第二章:戒指里的鬼影暴雨夜残留的铁锈味还卡在牙缝里,我盯着左手无名指的婚戒发呆。
此刻,窗外阳光格外刺眼,戒圈寒光却冻得我指骨生疼。鬼使神差地,
我拧下戒圈内侧的绒布开始擦灰——三道阴刻字母“LYX”此刻正像毒蛇盘踞在指根。
我全身血液倒涌,
突然梳妆台抽屉突然滑落一张珠宝票据:“定制日期:2021.3.14”。
这是那年热恋期,谢川捧着我烧伤的左耳说:“刻名字太俗,你在我心里是独一份。
”那时我的心里万分甜蜜。根本来不及想,就同意了下来。而现在LYX,
这三个字母却成了我心中挥之不去的心魔。我真傻,到后来才知道那其实不是我。
一切的甜蜜都和我无关。门锁“咔嗒”一响,谢川西装革履立在玄关,
阴影爬满半张脸:“擦这么亮,等会儿签字好看?”拆迁进度表被“啪”拍在茶几上,
就连纸页边缘泛着血似的红光。谢川的话语没有一点温度,甚至带了一点点得意。
“下月拆你老家祠堂,签同意书省得你亲自动手。
”表格里“青石巷”被红笔粗暴打了一个大大的叉,
这红印就像那年父亲咳在墙上的血点子格外刺眼。戒指寒光割着视网膜,
我脱口而出:“林雨溪的肾好用吗?”谢川解领带的手一顿,钢表带反光刺进我眼里,
晃得我有点恍惚:“医院刚通知,你弟的肝源排到了。
”冰锥般的话语扎穿耳膜:“条件是先拆祠堂。”虾仁的甜腥味突然钻进鼻腔。
他捏着剥好的虾肉抵到我唇边:“乖,张嘴。”她不知道我甲壳类过敏吗?
然后谢川却没有退却的意思,好像必须要看着我亲口吃下去,他才安心。我还是张开了嘴。
为了弟弟的肝源,我必须忍着。要不然一切就都白费了。
甲壳类过敏的灼烧感瞬间从喉头炸开,我别开脸,虾肉擦过嘴角留下了道道红痕。
“肿起来更像LYX了。”他轻笑,指腹碾过我过敏泛红的皮肤,“她新药需要替身试敏。
”衣柜镜映出我肿胀的左脸,恍惚间,
我看见父亲在火场里拼命地怒吼:“别吃他们给的东西!”耳鸣轰响中,
拆迁进度表的红光漫过戒指的寒芒,LYX三个字母在视野里也仿佛流淌出血来。
第三章:废墟里的血债老宅祠堂还是如约被拆掉了。现在已成瓦砾堆,
钢筋从断墙里支棱出来,像父亲被压弯的肋骨。我在废墟里艰难地翻找母亲牌位,
碎砖划破掌心流淌出鲜血也浑然不知。因为我知道这是我该受的。若不是因为我,
祠堂也不会拆的。父母不会原谅我的。列祖列宗也不会原谅我的。而我,亦不会原谅自己。
只有让自己痛,才能拥有片刻心安。此刻半截焦黑房梁下压着父亲遗照。
照片背面褐斑蜿蜒——弟弟用血写就的“姐,别争了”洇透了纸背,
最后一笔拖出绝望的长尾。血书铁锈味混着砖灰呛进我的喉咙,
突然身后却传来一阵高跟鞋脆响。我回过头望去。
林雨溪此刻正裹着羊绒披肩站在废墟上居高临下地看着我,
苍白指尖点着拆迁合同:“补偿款三天前就打我卡里了。”合同签名栏是我的笔迹,
连“捺”尾上挑的弧度都分毫不差——那是当年谢川握着我的手练签名:“夫妻一体,
字迹都要像。”是呀,是很像。像到若不仔细看,连我都以为是我的字迹。真傻啊,
当年我因为没有学会他的笔迹还懊恼了半天。“对不起,我写的还是不太像。”“没事。
只要我的像就好了,证明我更爱你。”爱,多么可笑的爱啊。
爱到最后我连一个完整的家都没有了。连一个栖身之所都不剩了。
推土机在远处轰鸣将我的思绪拉了回来。灰尘呛得林雨溪突然剧烈咳嗽,她用帕子掩唇,
很快帕子上就染上点点猩红。她倚着断墙喘息:“多亏你的肾……可惜试药过敏差点害死我。
”突然,瓦砾堆里猛地窜出野猫,惊得她后退半步。披肩顺着肩膀滑落,
露出了她的后腰——那里纹着朵玫瑰,花瓣脉络竟是我捐肾手术的缝合疤!
“纹身遮疤好看吗?”我攥紧父亲遗照,碎玻璃扎进掌纹,我却再也感受不到痛觉,
因为这远没有我心里来得痛。“用我的肾,骗我的拆迁款,还要我替你的药送命?
”她弯腰捡披肩,项链坠滑出衣领——吊坠里嵌着张微型芯片,印着“肝源优先权密匙”。
她眼含笑意地对我说:“你弟的命在我手里。”她开始用鞋跟用力地碾弟弟的血书,
血书一点点开始变得褶皱,直到灰土吞没了“别争了”最后一点血色,“再闹,
肝源就喂狗了。”这时,祠堂残柱轰然倒塌,尘土漫过她病弱的笑。我咬咬牙,抹了把脸,
砖灰混着血痂糊满掌心,像父亲火化时飘落的骨渣。
第四章:透析机上的优先权密匙祠堂的碎瓦此刻还卡在鞋缝里,消毒水味就呛进我的喉咙里。
医院里,我看着弟弟躺在透析机旁,脸色青得像霉变的墙皮。
护士敲着账单:“肝源优先权密匙呢?下周再不用就作废!
”我摸向口袋——林雨溪那条项链早被丈夫收走,空荡荡的兜布粘着冷汗。透析管突然震颤,
弟弟抽搐着抓住我手腕:“姐…祠堂没了…”监控仪尖叫炸穿耳膜,
恍惚看见推土机碾过父亲遗照。医生冲进来吼:“密匙不激活,他熬不过三次透析!
”走廊尽头闪过羊绒披肩的影子。我追到VIP休息室,林雨溪正把项链贴进读卡器。“滴!
优先权已启动”的电子音刺得太阳穴直跳。她晃着咖啡杯:“这玩意儿抵你半套拆迁款呢。
”突然抓住她手腕:“肾还疼吗?我的血在你身子里造反了吧?”咖啡泼上她真丝裙,
褐渍漫成我取肾的刀口形状。她甩开我冷笑:“多亏你试药过敏,新肾排异反应轻多了。
”抢救室红灯骤然亮起,护士举着沾血的透析管冲出来:“针头脱落!病人失血!











